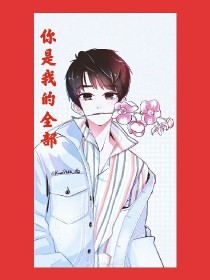第十二章
一
潘丽美摇晃着走出寻梦园雅间,来到餐厅的值班经理办公室。
今晚当班经理是一个名叫高燕的姑娘,年龄不到二十岁,半年前还曾是大餐厅里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端盘服务员。在一次列行公事的检察工作中,潘丽美发现她素质不错,头脑反映敏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不像大多数服务员那样见了高层领导慌恐不安或者忸怩作态,而是不卑不亢,眼神里透着某种说不出来的自信。潘丽美觉得这个姑娘很有培养潜力,第二天便一纸令下,让她做了餐厅值班经理。虽说这不过整个酒店里的最低一级的职务,但它同时也是进入大厦领导阶层的第一道门坎。更何况潘总经理用人一向不讲论资排辈,高燕深感知遇之恩,从心里佩服潘丽美,并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人生榜样。当她看到潘总经理进门时走路摇摆不定,一脸惊惑,总经理从来没有在手下工作人员面前失态过,今晚她——
高燕跑上前扶潘丽美坐稳,马上关好屋门,端过一杯凉开水。潘丽美摆手没接,竭力眨定着飘惚迷蒙的眼睛,问:“负责寻梦园雅间的服务员是谁?”
“李园园。”
“这个人作事怎么样?”
“性子慢一点,但人很老实,作事非常认真。”
“好,你去把她找来。”
高燕脸上现出不安,看到潘总经理掐着太阳穴紧闭起眼睛,犹豫了一下,匆匆跑了出去。
她带着李园园回到办公室,发现潘总经理弯在门后,手指伸进嘴腔,正冲着痰桶嗷嗷呕吐黄水。她赶紧上前帮她拍打后背。
李园园吓得不知所措,傻愣在那里,就像是自己闯下了什么大祸。
潘丽美直起身子,用高燕递过来的那杯凉开水漱了漱口,长舒了一口气,坐回沙发椅上。她的脸色苍白,眼睛里充满血丝,不过精神似乎比刚才好了一些。她问李园园:
“寻梦园客人喝的酒是你送过去的吗?”
李园园惊恐不安望着潘丽美,想了想,回答:“五粮液和法国红是,那瓶XO是杜主任自己带来的。”
“噢,是这样。这么说从餐厅上的两瓶酒是你给开的封,对吗?”
“是的,不过,这酒也是杜主任从家提前拿过来的,他说今晚是个人请客,钱能省一点是一点,让我装作是从餐厅现上的。”
“我没猜错。好吧,”潘丽美招手让高燕和李园园站近一点,神情十分凝重,说:“这酒有问题,很可能有人往里面掺了什么东西,所以,等杜主任他们一离开,高燕你准备好三个塑料袋,把桌上的三瓶酒封好交给我,记住,里面的残酒哪怕是一滴也要保存好。李园园,你用最快的速度将寻梦园收拾干净,不管任何人问起此事,包括杜主任,你都要装做不知,就说按平时一样将剩菜剩酒倒掉了,记清楚没有?”
高燕和李园园表情严肃地连连点头。
杜本正下了楼,返回到一层餐厅,直接来到了寻梦园雅间,发现里面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就问立在门口的李园园:“我带来的那三瓶没喝完的酒呢?”
李园园装作不解的样子,说:“什么酒哇,桌子都翻在地上了,我让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啦。”
“扔在哪儿?”
李园园带着杜本正来到餐厅厨房后面,远远地指着专门装残羹剩饭的长方形铁垃圾箱,说:“都倒在了那里面,你自己去找吧。”
杜本正不好意思地笑了,说:“这酒可都是好酒,我还打算把剩的那点带回去喝呢,即然已经扔了,就算了吧。”
杜本正离开餐厅,来到大厦的外面,看了看表,时间是九点十分。他没有上楼,步行走到街上,招手打了一出租,弯腰钻了进去,对司机说:“去火车站。”
在站前广场上,杜本正来回转了两圈,便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尾随过来,贴着他的肩膀小声问:“先生住店吗?”
灯光很暗,杜本正看到她脸上抹着厚厚一层的粉脂,白凄凄得如同戴了一副面具,只有那双风情万种眼睛像两把钩子扫来扫去,看来她正是他来此寻找的那种散逛的“野鸡”。他说:“不住店,只想过过站。”
“过站?”她贴紧杜本正,小声又问:“先生打不打洞?价格很便宜。”
杜本正睥睨了她一眼,就像个行内老手,问:“便宜是多少钱?”
“两小时五十,您若嫌贵可以再降一点。”
“去,再找来一个,要听话的,跟我走,一小时付你伍佰。”
她像终于抓到了一条大傻鱼似的,眉开眼笑地搂住杜本正的胳膊,不敢相信地问:“先生一玩二?莫不是耍我吧?”
杜本正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大票,举到眼前用手指咔咔弹了两下,然后插进她的领口里,说:“记住,听话还有小费。”
她立刻左右观望了一遍,朝黑暗中喜滋滋地喊道:“小菊、小菊,过来一下。”
杜本正带着两个从站前广场找来的妓女,打车回到了丽都大酒店。
下了车之后,她俩跟在杜本正的身后,望着华灯四射的摩天大厦,就像来到了天堂跟前咧嘴傻笑。“这地方我们还从来没有进去过呢。”
杜本领着她俩从便门进入大楼,没有坐电梯,而是选了很少有人走动的台阶楼梯,迅速蹬到六层。他让两个女妓在楼道的卫生间等着,自己先取出钥匙悄悄找开房间的门,摸黑走到里面,小声叫了两遍:“为民,马老兄,睡了么?”里间卧室里除了震耳欲聋的鼾声,没人答应。杜本正放心地拉开灯,走进套间卧室。他看到只有周一凡一个人背朝天地趴在床上,睡得像头死猪,而对面的床位却是空的,一惊,左右扫寻一遍,又打开卫生间的门朝里看了看,发现根本没有马天宝的影子。难道他真的留在了姓叶的那个女记者的房间?杜本正退了出去。
他来到张慧铃住的房间门前,敲了两下,叫:“叶记者,叶记者。”半天才听到里面应了一声,张慧铃穿着睡衣打着哈欠拉开门,见是杜本正,忙让进房间。“原来是杜主任,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杜本正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马上一边往外走,一边点头哈腰地说:“今晚大家喝多了点儿,我不放心上来看看。石老兄他——?”他发现卫生间的门开着特意朝里面瞅了一眼。张慧铃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他早走啦,若能是在我这里找到他,今晚你的酒也算是没有白喝呀。”
杜本正像被看穿了心思,连忙加快退出的脚步,不好意思地说:“哪儿的话,石检察官的为人谁不清楚?正人君子嘛。你休息休息。”
他只好又回到了周一凡住的那间客房,并叫上了一直躲在楼道卫生间的那两名妓女。她俩明显是头一次走进丽都,既紧张又新奇,乖乖地跟在身后,四下打看的目光也是偷偷的,就像两个初进课堂的小学生。她俩立在卧室的屋地当中,一会儿看看熟睡在床的周一凡,一会儿瞅瞅坐在沙发上心事重重闷头抽烟的杜本正,疑惑不解,忐忑不安,不知所措地等候指示。
杜本正终于站了起来,在烟灰缸里狠狠捻灭烟蒂,指了指床上的周一凡,说:“你们俩就搞他。”便走出卧室并在外面反锁上房门。
他匆匆来到一层自己的办公室,没有开灯,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一台照相机,对着地面试了试闪光灯,又按了一下快门,感到一切正常之后,将照相机放进一个皮包里,重新又回到了六层。
他用钥匙打开那间客房反锁着的门,闪进之后,径直来到套间卧室,发现那两个妓女仍穿戴整齐地立在床头,正窃窃私语。他绷起面孔,问:“你俩的动作怎么这么慢?”
那个叫小菊的妓女年龄小一点,胆子稍大,故意用力推了两把周一凡,皱着眉,说:“他浑身上下都是酒味,醉得像滩泥,怎么搞哇。”
“我们怎么弄他都不醒,莫不如还是你来吧。”另一个说着就凑上来。看来她实在不想错过这笔谈妥的买卖。
杜本正把她推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分成两份摆到身后的窗台上,说:“弄不弄成,我不管,但是若想拿走这钱,你们两就是装也得给我装出样子来。听懂了没有?”
“我明白啦,你这人是口味格路,就是看比干还有劲对不对?不就是作作样子么,好,我们就作给你看。”妓女小菊说着,就开始脱身上的衣服。
另一个当然更想得到那笔垂手即到的伍佰块钱,一边脱,还一边提醒杜本正:“别忘了,你还说有小费呢。”
杜本正嘿嘿干笑两声,说:“这要看你们合作得如何啦。”
他并没去观赏面前的两位越来越鲜明的裸体,而是走到了外间,从包里取出照相机,等了片刻,问了一句:“准备好了没有?”
“好啦,你快过来看满意不满意。”
杜本正将照相机藏进身后,装出背着手的样子走了进去。
她俩把睡得跟死猪一样的周一凡扒得精光,并压在了那个一丝不挂仰面而卧在床上的小菊身上,另一个光溜溜地跪在一旁,笑嘻嘻地问:“这样行不行?”
杜本正走到跟前很认真地左右看了一遍,发现这种姿势无论如何也拍不到周一凡的面部,便继续背着手说:“你和他换个位置,让他躺着,你在上面。”
她俩上下同时用力把周一凡推到一边,又努力抬着尽量摆到床的正中央,然后小菊骑在了上去,并很认真地找准位置,故作逼真地一上一下动作起来。
杜本正后退两步,从身后取出照相机嚓嚓嚓嚓连续拍了几张。
那个叫小菊的妓女没有料到他要拍照,一下子跳下床,过来伸手要抢杜本正手里的照相机。“你拍照可不行,我们日后想做人都难啦,把里面的胶卷快曝喽。”
杜本正躲闪着跷脚高举起照相机,两个赤裸的妓女像两条光溜溜的鱼前后跳跃。
“笨蛋,快给我住手,我是从后面拍得,谁也看不出你们是谁!”
那两个妓女半信半疑地看着杜本正。“你是在骗我们?”
杜本正将照相机交给了小菊,并让另一个坐到床上的周一凡身上,说:“不相信你自己看看。”
小菊举到眼前看了一阵发现里面除了能看清那个男人的脸外,女的还真只是一个光溜溜的背影。
她感到十分有趣,并还亲自拍了几张。
但是,她忘记了在杜本正拍的那几张里,跪在一旁的那个妓女脸部却正侧面均被拍进了镜头。
二
黎明时,马天宝从昏睡中醒过来。他以为仍是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感到脑袋里面发沉,周身疲惫,便没有撩开眼皮,让朦胧的睡意继续像棉絮一样飘惚。
十分钟过去了。他想侧身动一下,但没有成功,脑袋如同固定在了潮乎乎的枕头上。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勉强睁开眼睛,看到房内幽暗,从窗口照进的几丝微弱的光亮,像影子似的拖在地上。他先看到了一双脚,顺着脚往上,发现有一位扎着白色佩带的交警斜靠在床前的椅子上,怀里抱着同样是白色的头盔,歪着脑袋睡着了。
他认出这位交警正是王鹏的儿子王晓川。
同时,他还发现周围的环境并不是家里,而是某个医院的病房。一惊,他猛地坐了起来,头部一阵剧烈疼痛不由得“唉哟”一声。叫声惊醒了王晓川,他赶紧站了起来,俯身双手扶稳马天宝的肩膀。“睡醒了,感觉怎么样?”他问。
马天宝闭上眼睛尽量放松头部,让疼痛感慢慢减弱。他再次睁开眼睛,用手试探着轻轻摸了一下脑袋,上面裹了厚厚一层的绷带。他疑惑不解地问:“我出车祸了?”
王晓川嘴角微微笑了一下,看到马天宝已经坐得很稳,这才松开手坐回到椅子上。他说:“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只不过你的城市猎人挡风玻璃碎了,还有左侧的大灯,被对面货车的保险杆刮报废啦。你的车,我已让一个朋友拖去修了。”
“有没有伤着人?”
“没有,就是你自己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
马天宝心里舒了一口气,仔细回忆起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然而就像作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梦一样,除了隐隐约约还记得曾在丽都大酒店吃过晚饭,其他的事情竟没留下一丝痕迹。
“昨天的事情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晓川,你是怎么赶到出事现场的?”
“昨晚我在广场值班,10点钟下岗,路过建国时正赶上你的车出事儿。石检察官,无论如何我也得提醒你一句,以后再可不能酒后驾车了,雨天路滑,若不是你对面的那个司机反映比较快,恐怕你的命就保不住啦。”
“我喝酒了?”马天宝像是问自己又像问王晓川。
“没错。没喝酒,就是初学开车的人也绝不会跑到左侧超速行驶,除非他不想活啦。”
马天宝很难想象自己竟会像一个疯子,在雨夜里驾着城市猎人逆流超速而行。如此看来他不仅是喝酒的问题,而且大脑也丧失了理智,如果说是在丽都喝的酒,出事的地点却是建国路出口,与回家的路线正好相反,我是要去哪里?
“医生说你的头部是外伤,里面没什么大事,8点钟交换班的时候再检查一下,然后就
可以出院了。至于你的城市猎人,修好后我让人给你开到单位。”王晓川打了一个哈欠,揉着眼睛站了起来,说:“我先回去告诉一声,我母亲听说你出了车祸还一直担心呢。”他走到房门口,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扭过脸笑着告诉:“昨晚有个姓江的女孩一直打你的手机,一听到你出车祸吓得直哭,后来才发现同住在一个医院里,她跑过来陪了大半宿。用不用我去把她叫来?”
马天宝这时才想起来昨晚是要去东城区急救中心,去看江心婷和她的母亲,这起不大不小的车祸险些误了大事。他连忙摆了一下手,说:“别去叫,她母亲病得很重,我一会过去看
看。不知道她在哪个病房?”
这时候门开了,王晓川一看来人乐了:“人已经来了,正好打我的替班。”
果然是江心婷走了进来。
马天宝发现江心婷的脸色十分憔悴,眼睛红红的,嘴唇灰暗,明显是睡眠不足疲劳过度的样子。“你母亲怎么样?”他问。
“她好一些了,刚刚睡着。你的头还痛吗?”江心婷孩子似的愧疚望着他的满头绷带,一边问一边用手轻轻摘去粘在上面的发丝,同时眼窝里又涌出泪花。“都是我不好,让你急着赶来,否则也不会出事。”
马天宝向后挪了挪身子,拉江心婷坐到床边,给擦净脸上的泪痕,拍了拍她的脑门儿,笑着安慰道:“这跟你没关系,全是因为我酒后开车,活该!”
江心婷微微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说:“你就会安慰人家,我不打电话,你也不会喝酒之后还要开车的。”
说到酒后驾车,马天宝始终百思不解,他已经慢慢地回忆起来,昨晚一块在丽都喝酒有周一凡、张慧铃和杜本正,他自始至终喝了还不到半杯XO。这种洋酒他过去也曾喝过,还从来没有出现这么大的反映,他又记起周一凡这个有名的“造一瓶”,酒喝的还不到平时一半的量,便醉得几乎不省人事,难道真的是因为昨日营救叶婉造成过度疲劳的缘故?
在他走神儿的这一会功夫,江心婷端来一盆温水放在了椅子上,在里面搓湿毛巾,铺展在手面上,小心翼翼地开始擦拭他脸上残留的血迹和乌泥。她每擦一次,都先要用毛巾蘸一下盆里的水,浸湿凝结的血点或泥斑,以免用力引起疼痛。她细心得就像一个正在作手术的外科医生。马天宝觉得自己脑袋只受了一点皮外伤,四肢灵活,手脚能动,却像个脑瘫患者让一个小姑娘如此照顾,未免小题大作。他本想拒绝。但是他没有。他闭上眼睛,就像用心去捕捉失却多年的一种生命中极其宝贵的东西,那是一种完美家庭中的温馨,一种亲情中的爱意,此时此刻,他像儿时依偎在母亲的身边,那种松弛无忧无虑的感觉,仿佛整个身心都浸泡在温水盆里。
“马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头很痛?”江心婷恐慌地抓住他的胳膊摇动着,焦急不安地说:“用不用去叫医生?”
马天宝瞅着江心婷就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良久,才摇摇头,语调沉重地说:“谢谢你,江心婷。”
江心婷不解其意地愣了一下,问:“谢我?马大哥,你怎么忽然说起这话?”
马天宝笑了,拍了拍她的头,说:“你还小,长大了就明白啦。”
江心婷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脸蓦地红了。她掉过脸去,小声反抗道:“你总是小看我,应该学会平等待人嘛。”
马天宝下了床,活动了一下胳膊,说:“走,江心婷,去看看你的母亲。”
他们俩来到了江母的病房。
老太太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似乎睡得很实,高高吊在床边的静脉注射液,通过一根透明的细管仍在悄无声息地滴打着。几日不见,马天宝发现江母突然消瘦许多,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眼仁儿深深凹进眼框里面,嘴唇颜色紫黑。他联想母亲病逝前的情景,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老太太恐怕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他把江心婷叫到病房外面,问:“医生最后是怎么说的?”
“说是脑瘤压迫中枢神经,造成间歇性全身抽搐,今天要请专家来给会诊之后,才能最后决定是否开颅手术。”
“江心婷,你要有思想准备,”马天宝犹豫了一下,把手放在了江心婷的肩上,说:“老太太年龄大了,又有心脏病,开颅手术风险很大,你要坚强些。”
江心婷埋下头,双手捂住脸竭力控制着自己,哽咽着说:“我知道,马大哥,我哥的死对她打击太了……”
“婷,婷婷。”病房里传来江母微弱的叫声。
他俩赶紧走进病房,来到老太太的床前。江母发现了马天宝,喘息着说了一句:“石同志,你终于来啦。”便挣扎着要坐起来。马天宝慌忙拦住,坐到床边上,说:“大妈,对不起,我路上出了点事,来晚了。”
江母吃力地转过脸,瞅着马天宝头上的绷带,问:“孩子,你这脸是怎么了?是不是被那些坏人打的?”
“放心吧,大妈,我这是自己不小心碰的,没啥事。”
江母抖颤抬起挂着静脉注射的胳膊,紧紧攥住马天宝的手,眼睛忽然睁大,由于激动喘息更加吃力:“孩子,你是个好心人,大妈有件事想托咐给你——”
“大妈,您别着急,有话慢慢说,只要我能做到,您尽管放心。”
“我的日子不长了,可是婷婷这孩子还小,我死也放不下心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答应我,把婷婷就当做你自己的妹妹,由你照顾她,我死了也心安哪。”
“您安心养病吧,江心婷的事就是我的事,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尽力帮您照顾她。”
“好,孩子,你答应大妈了是不是?这我就放心啦,我在九泉之下报答你的恩情。”江母把脸转向江心婷,眼里含着泪水,说:“婷婷,你跪下。”
“妈——”江心婷泪流满面跪到床前。
“你都听到了,妈不在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听你马大哥的话,记住没有?”
江心婷点头答应。
“好,你替妈给你马大哥磕个头吧。”
马天宝赶紧拉起江心婷。“大妈,您千万别这样,从今天起江心婷就是我的亲妹妹,我一定照顾好她,您就放心吧。
老太太哆哆嗦嗦从怀里取出一个存折,放在马天宝的手里,说:“这钱我一分没动,你们自己留着将来好用。”
“妈,你不会死的……”江心婷抱住母亲大哭起来。
三
上午8点30分,交接班的两名医生带着一群护士来到马天宝的病房,检察了体温,又拨开眼皮仔细看过瞳孔,让他在屋地当中来回走了两圈,说:“你签个字,可以出院了。”
这时,张慧铃从外面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
她看到行动自如的马天宝,瘫坐在病床上,长长地“唉”了一声,说:“你快把我吓死啦。”
马天宝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的消息?”
“我昨晚一直不放心,早晨起来吃饭,潘总就告诉我说你出车祸了。我还以为你上八宝山了呢。”
“我的级别不够,就是死也进不了八宝山。好家伙,这消息传得可真快。”
正说着,门外又进来两个人,一个是检察院的办公室魏主任,一个是汽车司机小关。魏主任表情很严肃地上下打量完马天宝,问:“ 没什么大事吧?”
马天宝指了指裹满绷带的脑袋,自嘲地说道:“事儿倒是没有,不过这副残兵败将的样子,恐怕要在家猫上两日。”
魏主任犹豫了一下,说:“没事就好,还是先回单位吧,陈检察长急着要见你。”
“什么事这么急?”
司机小关笑嘻嘻地说:“事儿肯定不小,陈检察长大发雷霆,说只要马天宝不死,抬也给我抬回来。”
马天宝走进陈检察长办公室。
他看见周一凡耷拉着脑袋坐在沙发上,陈检察长气呼呼地来回走着,脸色铁青,夹着雪茄的手指不停地抖颤。看来陈检察长的火气已经蹿上了房顶,小周成了第一个挨收拾的靶子,到底出了什么事惹得老总发这么大的火?
陈检察长抬头看见马天宝,火又上来了,指着他的脑袋,说:“你、你看看你什么样子!”
马天宝坐到周一凡身旁,作出一副甘心受罚的样子,嘻皮笑脸地说:“陈检察长,干吗发这么大的火,气大伤身,批评是对的,保护革命身体也很重要嘛。”
“马天宝,你给我严肃些!”陈检察长狠狠拍了一下写字台,一屁股坐进后面的转椅里,点着他们俩的鼻子,骂道:“你们这两个混蛋,案子没弄出结果,却捅出这么大的娄子!
周一凡,你给我站起来,你自己说,叫我怎么处理你?”
马天宝感到问题严重,悄悄捅了一下周一凡,问:“出了什么事?”
周一凡抬起头,脸色惨白,站了起来。他没有理会马天宝,看了一眼陈检察长,说:“我无话可说,您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你说也没用,证据就摆在这里,而且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不处理你也不行!”
马天宝发现陈检察长的写字台上放有许多彩色照片,连忙走过去,一看吓了一跳,那些照片拍的都是做爱的场面,而且不堪入目,一男二女,那男的不是别人,正是周一凡!马天宝也火了,一把揪住周一凡的衣领,摇晃着问道:“一凡,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你说呀——”
周一凡望着马天宝,眼里不知不觉流出两行泪水,“石兄,对不起,我……”他抹了一把眼睛,咬住嘴唇,无奈地摇摇头。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马天宝放开手,抓住周一凡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一凡,我相信你的为人,你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上班才知道这件事,至于这些照片是怎么拍的,我一点都不清楚。”周一凡恨恨地打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蹲在了地上哽咽地说道:“我昨晚是喝多了,也是在丽都住的,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这两个妓女是怎么回事。”
马天宝想到自己的这次莫名其妙的车祸,猛然意识到昨晚发生的一切一定是有人阴谋陷害。眼下案情进展正是到了关键时刻,针对他和周一凡接连发生的怪事,显然是对手已经开始反扑。他走到陈检察长的面前,拿起那些照片仔细看了一遍,发现所有照片上的周一凡都是闭着眼睛,竟没有一张是睁开的。不过,除了了解真相的人以外,其他人看了会作出另外的一种解释。
“陈检察长,请你相信,小周他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一定是有人趁他喝醉的时候,制造的假象。”
陈检察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什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啦,有人把这些照片举报到了市委、纪检委,还散发到了报社、电视台,从早晨到现在,询问核实的电话就没有断过。检察官嫖娼,就是新闻界不给你曝光,也会传得沸沸气扬扬。”
“陈检察长,院里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
“按党员干部的处理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小周是被人陷害的,能不能拖一拖,等了解清楚再作处理?”
“不行,反响这么大,不马上处理,检察院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咱们是反腐机关,自己的腐败问题都处理不了,还谈什么反腐倡廉!”
“我个人认为院领导这么作未免有些过份,明知陷害还要把人一棍子打死。”
“过份?你的问题我还没谈呢。”陈检察长从抽屉里掏出马天宝的工作证和一张罚款单,往写字台上一丢,说:“检察官驾车不遵守交通规则,还拒交罚款,又撞车差点闹出人命,马天宝,你在搞什么鬼明堂!”
马天宝没有解释,陈检察长说的都是事实,要怪就怪自己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拿起工作证和罚款单,沉吟片刻,恳求地望着陈检察长,说:“能不能给小周一次机会,让他跟我把这个案子搞完?”
陈检察长既没否定也未答应,而是瞪圆了眼睛盯着马天宝,问:“给我说老实话,你是不是擅自进过康泰药厂搜查?”
马天宝一愣,避开陈检察长咄咄逼人的目光,同样是既没否认也未承认,而是反问了一句:“怎么又有人告状了?”
“我警告你,马天宝,咱们是执法部门,绝不许搞非法活动。”
“说我搞非法活动,我倒很想看看他们有什么真凭实据?”马天宝冷笑了一声,说:“陈检察长,您可不要听信那些无聊的谣言。”
“谣言?你们两个给我听着,昨天办案领导小组开会,秦局长对你们的查案行为非常不满,特别是你——马天宝,枪杀案不好好弄,非又扯出一个什么毒品问题。人家怀疑你是公报私仇,打击有能力的企业家,破坏我市的投资环境,造成美方对我们极不信任,要撤资,终止合作,马天宝哇马天宝,你有几个脑袋,这么大的责任别说你一个小小的检察官,就是东西两院的领导也担当不起呀。你还说什么是谣言,没有一点组织观念,完全是个人英雄主义!”
马天宝意识到已经有人开始向陈检察长施加压力,看来田照东这帮家伙的势力还真不小,上下一齐反扑。“是不是已经有人提出来,要求撤换办案人员?”他问。
陈检察长的火似乎发泄得差不多了,叹了一口气,掏出雪茄烟叼在嘴上,又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红塔山,给马天宝和周一凡每人扔过来一支,说:“提了,还是市委的意见。”
“秦局长是市委常委,又主管公检法,其他领导当然要尊重他的意见了。”马天宝不禁嘿嘿冷笑了两声,说:“我就料到他们早晚会搬出秦海林这块牌子。”
“马天宝,你可不能随便怀疑领导同志,秦局长提的意见也是从全市的大局出发。我们是执法者,更要有组织观念。”陈检察长皱着眉头,狠吸了两口雪茄,说:“刘书记、关书记和我都不同意中途撤换办案人员,最后秦局长也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再也不能给我惹麻烦啦,作事最好要小心点儿,一旦被他们抓住把柄,我可救不了你!”
“放心吧,我已经揪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剩下的问题就是让他们认罪伏法。”马天宝看了看身边垂头丧气的周一凡,转向陈检察长说:“小周的事还请您手下留情,最好让他协助我把案子搞完。说实在的,案情能查到今天这种程度,为民有百分之九十的功劳。”
陈检察长摆摆手,恨铁不成钢地瞪视着周一凡:“不给你一个教训,也改不掉你这贪杯的臭毛病。处理决定不能改,但可以留职察看一年,你暗中继续协助马天宝查案,等一切真相大白之后,再考虑恢复公职问题。”
天宝引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你好,土豆小姐
- 简介:你我皆是土豆小姐
- 1.1万字1年前
- 祭奠纯白
- 0.2万字1年前
- 生理爱情
- 简介:江宇:“对不起,无乐,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乔斯特“爷教你打枪,你教爷怎么让你喜欢上我好不好啊!”K“我喜欢男人,你是男人,懂了吗。”左云“阿顾,我只希望你是我一个人的,除了我,别人都不可以”
- 1.0万字12个月前
- 风暴侦探犬小五(二)隐匿的青莲秘市
- 简介:【已完结】~谢谢大家的支持~₍˄·͈༝·͈˄*₎◞̑̑鸡犬组合不辞辛苦赶到印度,一番调查之后,终于找到了开往青莲秘市的“不存在的列车”。从坐上那趟超乎想象的豪华列车开始,一连串的遭遇都不断地冲击着小五和普普的认知——一只使用欺诈手段的蝙蝠携带的违禁品居然是合法的?身为动物之王的狮子却哭哭啼啼的被其他动物肆意欺负?列车的目的地竟然是一个行踪不定、地图上没有标识的隐秘“黑市”!那里到底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还是无数动物们向往的“希望之地”呢?嘘——小心!秘市的神秘主人“斗篷先生”就隐藏在周围动物之中,一旦上了他的黑名单,就会陷入一场噩梦!当鸡犬组合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陷阱时,已经来不及了……被定下了天价的普普,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 6.3万字10个月前
- 你是我的全部1
- 0.2万字9个月前
- TFBOYS之纯心虐恋
- 简介:十年,我们终于回来了!——穆然曦,慕容雪,欧阳夏丹。十年了,我们终于等到你们了——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
- 0.4万字9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