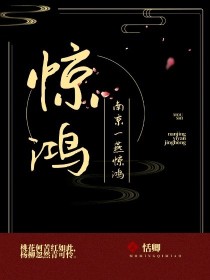第八章 病入膏肓
朝堂上一片死寂,那几颗悬在城门上的人头太过凄惨,于他们眼里挥之不去,永生难忘。
他们也是安逸了许久,不清楚继位七年有余的天子究竟是何种模样的,竟还与先前一样尸位素餐,被忍无可忍的天子除干净了,如今底下的臣子各个心怀鬼胎,不敢揣测圣意,低着头等着阁老替他们发声,倒是狡猾。
梁霁未曾理会他们的想法如何,只是高兴,险些收敛不住情绪在这大殿之上笑出声,冠冕遮住他莫测的神色,却挡不住他的视线,他第一时间去看他的好弟弟,见其冷静自持,似乎并未想在着大殿中开口。
也似乎是清清白白,未尝与他们相勾结。梁霁微眯着眼,朝着旁边的郝阿睿极其轻微地动了动小指。
宗朝踏出几步,扬声道:“有事禀奏,无事退朝——”
余彬彦快步走至中央:“臣有本奏。”
梁霁挑眉,好奇这老东西会说些什么,面色如常地点头:“说。”
“不知季里贤与赵知谐二位大人是如何定罪臣之罪的,又以何种依据先斩后奏,将其满门抄斩?”余彬彦礼节到位,问得也十分有水准,就连梁霁也难以找个理由降罪于他,“究竟是大公无私,还是另有所图?”
“近日诸位爱卿政务繁忙,六部、内阁皆忙得不可开交,不如让朕替余阁老解惑,”梁霁笑吟着将备了许久的折子交给宗朝,“季里贤与赵知谐二人都是依朕旨意办事,至于罪臣之罪自有的公证——宗朝,念吧。”
“平阳御史兼县令潘直库房私藏万万官银,皆从军粮中私扣,七年农忙低价收粮,高税薄利,百姓苦不堪言,有击鼓鸣冤者被活活打死,有民逃难临城却因其结党营私含恨而死,以致乱葬岗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欺君罔上,结党营私,罪该万死,当满门抄斩。”
“邺城府主肖赞与当地皇商暗中勾结,坑害清白的寒门学士,会试中命人恶意纵火嫁祸于人,以公谋私,不利朝政,藐视皇权,罪大恶极,念其城内百姓还算安乐,但死罪不可免,特赐一杯鸠酒自行了断,其余赐白绫百段,女眷充军妓…”
余彬彦仔仔细细地听着,镇定自若,十年入内阁铸就了他这幅大难临头面不改色的面皮,丝毫不见急切之色。
梁雩一心二用,听着公证不发一言一边细细梳理先前所得的一切推测、证据,彻底地翻了先前的猜测——既然如此,是谁想要谋逆?
宗朝平静地念完折子,将其原封不动的交还于梁霁手中,退回了梁霁身侧,后者讥笑,慢悠悠地开口道:“八年前朕四处走访,甚至走过了整个中国,继位以后朕也不假人手,亲自问询了各方百姓,他们究竟是怎么过活的。众爱卿,给朕多添烦忧的蛀虫,还要朕宽宏大量地容下他们吗?”
余彬彦:“臣有一言,陛下日理万机,不是事事都亲力亲为,臣以为有不忠不义、意图谋反之人暗中勾结,威逼、利诱城中百姓、县官欺君,未尝不能。”
梁霁意味深长地打量着他,似笑非笑:“朕自有判断,于阁老眼里,朕是无能之辈否?”
余彬彦从善如流跪下,铿锵有力地表忠心,也不知是真是假:“臣不敢,只是季大人行事有失偏颇……”
梁霁打断了他:“阁老,都是朕的意思。既然阁老如此,不如朕退位让贤,这龙椅禅让给您坐?”
朝堂之上鸦雀无声,又见梁霁懒散地靠着龙椅,坐得不端不正,懈怠悠闲,一只手臂靠着扶手,撑起一边脸颊,珠帘摇曳。
可是,无人敢开口弹劾他行不端坐不正。
“诸位,老实本分做事,胜过险中求富贵,”梁霁似乎并未放在心上,方才不过是一句戏言,只是扫视着百位官员的头颅,轻飘飘地开口,“散吧。”
宗朝一声“退朝”宛若惊雷一般乍起,唤醒了神游的梁雩,他皱着眉,颇为从容地跟随百官出了崇光殿,见面色苍白的季盛走得很慢,先停住了摆驾的阿纷,上前扶着他:“季大人,可有恙在身?”
季盛专注着压制喉中腥甜,一时不察被吓了一跳,咳得撕心裂肺,眼下又一晃神,陷入了看不到头的黑暗中,直愣愣地栽下去。
梁雩揽着他的腰不叫他摔在地上,方才直直绷紧的一根弦彻底断了:“阿纷!传太医!”
黄御墨亲自出马为季盛切诊,神色愈发凝重。
霁、雩二位在旁静候,也跟着蹙起眉,出奇地一致,且跟彼此像了个十成十,黄御墨一晃眼又把人认错,冲着梁雩道:“陛下,季大人是五腑衰弱枯竭之相,臣只能尽力延长其寿命,至于痊愈,已是难如登天了,臣无能…”
“咳咳…”朝服还未褪下来的天子总搞不明白衣服颜色就能区分两人为何他还能认错,狠狠地咳了两声,“治好他有几成的把握?”
黄御墨调整方向认对了人:“药材上等够用就三成,否则两成。”
“尽力而为,孩子不能没有爹,”梁霁瞧了一眼形销骨立的季盛,直叹气,“药材从国库拨,无需过问。”
“养好后他就不能再奔波了,陛下,”黄御墨跪地叩首,“请陛下怜惜季大人,怜惜臣的病人。”
梁霁闭眼,拂袖背手而去:“赵知谐不知分寸,季里贤在侧可控制他的所作所为,阿睿不能离开朕,也只能委屈他了。”
黄御墨缄默不语,跪在地上不起来,梁雩见状理好衣摆,跟着他一起跪地:“臣弟愿替季奉天为陛下分忧。”
“哦?你与里贤认识?”梁霁亲手将季盛的乱发理好,轻轻扫了他一眼,“说说像样的理由。”
梁雩实诚地说:“京城事太多,十四日就休沐一天,还得晚睡早起,臣弟再不走怕是要忙疯了。”
梁霁:“就仗着朕惯着你。你在京城做事不是替朕分忧?况且这番去定是要跑断腿的,你打小就不好武,如今说是手无缚鸡之力都不为过,朕实在不放心你。”
梁雩:“这不是还有赵统领么。”
梁霁叹口气,将一封重新落笔好的密信交给他:“知谐有自己要做的事,朕需要你去办的是去查查这些,把握好分寸即可。”
梁雩一愣,问他:“那季大人?”
“朕自有安排,”梁霁摆摆手赶他走,“行了,你回去好好收拾府上内务,三日后启程前往奚城,其余的自己安排。”
“臣弟告退。”
黄御墨把自己当透明,末了还是忍不住偷偷瞄了一眼离开的梁雩,心里正期待天水能带着他上次的承诺找他,却冷不丁地被梁霁点名:“逍闲,现在如何?”
他暗暗擦了擦汗,答道:“臣方才施了几针,几息后方可苏醒。”
梁霁:“你先去抓药吧。”
黄御墨行礼退了,仅留二人在殿。这也是君臣之间仅有的一点点,能对彼此真情流露的时间。
梁霁:“里贤兄,你觉得如何?”
季盛确实已经醒了,如做了一场大梦,飘飘忽忽地躺在榻上,这才迟钝地察觉到自己的时日无多。
他静了一会儿,方气若游丝地应答:“不太好啊齐兄,孙姑娘她是不是被我这幅模样给吓傻了?”
梁霁淡淡一笑:“你糊涂了,孙小姐如今已是季夫人,是小弟赐婚。前段日子,你还说嫂子有了身孕,估计是挑着瑞雪兆丰的年头出世。”
“对,摇情…”季盛微笑,随即彻底清醒过来,侧头去看冠冕未来得及摘下的天子,“齐兄,给大哥一年吧,一年之后,大哥亲自送岳父上路……”
“你还未痊愈,还需静养,别想这么多,”梁霁亲昵地拍拍他的手,“再睡一觉吧。”
季盛难以置信,双眼圆瞪,死死攥着他的手:“小弟,答应大哥…求、求你…陛下——”
梁霁从容地掰开他的手指,其实也没用多少力,但最后在要紧的关头还是松了口:“最多半年。”
“够了、够了…”季盛得到答案,虚弱地喃喃,极为缓慢地收回手,“至少,还能同她和孩子过个好年…”
终于他再也撑不住,再次昏睡过去。
在此之前,一个声音渐行渐远,叫他于梦中都如坠冰窟——“阿睿,告诉黄院首,备足‘回春散’吧,半年的量。其他的就不需要了。”
山深闻鹧鸪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快穿之王爷是我的
- 简介:本文主要写了男主因喝酒过多丧命后重生到各个地点完成任务(任务主要以攻略为主)
- 6.3万字2年前
- 冷宫弃后逆袭记
- 简介:【十金币加更一章】遭人陷害,被心爱的人打入冷宫……冷殇陌你究竟是爱我还是厌我?冷宫的日子好难熬啊……馊饭冷食,还有其他妃嫔的蹂躏践踏……奴婢房里的各种欺辱……各种惨甚的刑罚……不!不!不!这些我受够了!要走出这里,何不弃情绝爱,载恨华丽归来?成为暗宫宫主,绝色医师,三国皇帝联手的挚爱!几番与皇帝的对决,【千雪寻笑言:“你真的爱我吗?”】【冷殇陌:“你愿意原谅我吗?”】
- 2.7万字2年前
- 凤栖凰
- 简介:璃倾舞:“你若负我,我会亲手杀了你。”墨子清:“好,我必不负你。”楚暮:“小师妹,他骗了你,你为什么不杀了他”璃倾舞:“因为……我爱他,就算他认错了人,我依然爱他”雪倾歌:“墨子清,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吗?魔族王上果真无情啊……”紫云涵:“子清,别理她,我们走”丢下满身是伤的璃倾舞走了雪倾歌:“倾舞,跟姐姐回去好不好”话语中有一种心酸璃倾舞用她苍白的唇说道:“姐,他会记起我的”转身离去,不带一丝留恋
- 0.5万字2年前
- 战败后,我成了德妃
- 简介:大女主剧情,专心搞事业的人,古代,不言情。
- 1.2万字1年前
- 燕惊鸿
- 简介:桑颜,一个前世家破人亡的世家千金。重生归来,她不再躲藏在深闺大院中,掌控全局,报仇雪恨。哪知,那传闻中的病秧子世子却对她一见钟情,开始不停的骚扰她。“病秧子”世子:阿颜,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病秧子”世子:阿颜,别走。“病秧子”世子:阿颜,你的手帕还与你。桑颜到最后发现,自己好像沉沦进他的温柔乡了?!
- 0.2万字1年前
- 栖枝欲叹宫墙柳
- 简介:我小时候就被教导着“瑾瑜啊,你以后嫁人,便是要作得威慑八方的主母。兰家虽是商家,还是可以为你搏一搏的。”我家姓为兰,字瑾瑜,是我儿时便为自己取好的,意思是花开不渝,祖母说了小鱼儿长大了定然...
- 0.5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