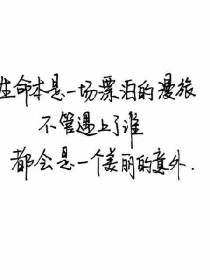第八十二章 空与沌 第二章·承
或许由于是我的外貌与少年相近,亦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我被送去了学校。
可我一谈到学校,便只是长叹一声呜呼!
学校简直是难以言说的恶魔之地,那里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自私的想法,明面上是为了学习,暗地里却是各种不堪入目,在我看来,这种地方毫不异于被扭曲的性欲的垃圾堆。
在日常,我必须去遵守那些老师们所认为的正确的道路来走,若是违背,便会引来极其严厉的惩罚,我并未以身试法,只是看过他人的经历,甚至我只道听途说,但我依旧感到恐惧至极,我无法预想若是我犯了错,我会有怎样残酷的后果,我只能战战兢兢,每日按照一定的章程来生活。
每日两点一线的生活,我并未有向其他人一样,去同学家做客,或是与同学在除学校以外的地方见面,尽管我并不太喜欢与他人聚会或是别的什么,但我却对这些事情感到渴望,但也只是一瞬罢了,毕竟待在自己房间里才是最安心的,固然会有他人闯入,但最起码大部分时间可以放松警惕……若是说得再朴素一点,那便可以直说成:床是人类最好的伙伴,躺一整天都没有关系。这种思想真的应该存在吗?还是说这是错误的呢?
在学校我寸步难行,我不得不将自己拘束于方寸之地,每日在自己座位上打盹,若是必须要起身,我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做完事情,然后回到座位上。对于那些来找我寻开心的,我也只是笑着向他们道歉,他们看我只知吃吃的笑,也便不再理我,或是把我当做发泄的工具。我默默地寻找着方法,来逃离这绝望的地狱,让我的真相不会被别人发现。
我认为这这过程是艰辛的,但也是美好的,我因此得以沉浸于疯狂之中,这如同暴风雨一般的攻击,使得我兴奋不已。似乎越是敏感的人,就越期待这暴风雨的来临。不过在兴奋带来的劳累之余,我也是发现,这是没有办法的。
学校的生活是极其无趣的,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那些老师按照上面的想法,向学生灌输着教条,把学生的思想束缚起来,从而稳固上面的统治,上面的他们不会管他们的子民如何,他们只会自己享受,然后欺骗着民众,我不知道那个最顶上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但最起码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而民众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面里顺从着,背地里又是另一种样子。
不过所谓“自由民主”,好像也确实如此,我们无法说任何他们不喜欢的话,我的嘴被他们缝起来,我的身体被他们摧残,或许,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早已失去信心了吧?尽管如此,我仍需要应付如作业之流或是所谓“同学”的无知所云的攻击。我没有招惹他们,又或许是。我根本不知道我有没有招惹到他们。
一层层的剥削,一层层的变本加厉,一层层的向上反抗,不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就这样漠然的如同木偶一般默默无言,随着身边的人潮,向着时间的终点走去。我感受着身上的伤痕,我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但它们的产生,必定是因为我是有罪的。
浮世皆苦,苦有万般,但如果要说什么叫做残忍,那或许就是全世界与我为敌。
大概是什么时候,我已经记不清了,或许是中学的时候,亦或是所有时候都有发生,这种事情或许并不应该拿出来说,但我又凭什么去掩盖我作为罪人的证据呢。
当时我和他们为首的人同姓,名字也很像,似乎是这样的,我已经记不太清了。(看啊,我竟连这种事都记不住,实在是太可笑了。)他们是老师口中的“流氓”,我并不认为是这样,我反而认为他们反而是如同天使一般的,点醒我的人。
我记得那时候,我因为某些原因,住在学校里一段时间。学校是有宿舍楼的,住在宿舍里,男生和女生的寝室中间只隔了一堵墙。
我并不太喜欢这样的生活,每天都被别人窥视着,这种窥视感让我十分烦躁,而且宿舍的设施十分简陋,简直就不像是能住的样子,于是,我只求这种日子能快点过去。
我的寝室在3楼,而他们的寝室在2楼,不知为何,他们居然会这么巧的住在一起,但或许住在一起,他们才会聚在一起吧。
有一次我经过2楼,看到他们寝室门口围了很多人,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我并不想去凑热闹,于是我转身便走,上了楼。在楼梯间,我隐约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但他们似乎跟了过来。我逐渐加快脚步,而他们也随着加快速度,随后我们越来越快,在楼梯和走廊里跑了起来。
我躲进了房间里,但门没有锁,这个门实在是太旧了,就像我的灵魂一般破陋,无法修治。
他们闯了进来,把我围住,此时周围并没有其他人,我窝在墙角,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只能低着头,我不敢看他们。
“真是个乖巧的好孩子啊。”
是这样的吗?我不得而知,这样无法思考、不会反抗的的我真的值得称赞吗?
他们冲上来,将我压在身下,蒙起我的眼睛。我不明白他们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是仅仅为了美观或是有趣而存在的装饰物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或许还算是懂得所谓“美”的人啊。我还没来得及思考更多,他们便将什么东西插进了我的身体,我并不清楚他们在对我做什么,我只剩下一种奇妙的触感,如同海浪般拂面而来,触感却像刀割一般,空气中弥漫着苦杏仁的气味,我不自觉地抱住了他们,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想着,他们或许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吧?那我这样算不算在疗愈帮助他们呢?但他们并没有笑啊,所以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呢?
我应当是昏迷过去了,随后我清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我整理好凌乱的衣服,擦了擦嘴角的液体,随后铺了床,便去上课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给别人造成麻烦,希望没有。
后来一连几天,他们都对我做了同样的事,同时他们还给我找了一份兼职,似乎是去做什么“兔子”,也不过是做差不多的事罢了。不过似乎同行也大多是有相同经历的人,但我并没有和他们很好地相处,或许是因为观念不合,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的错。
也不知是因为谁,后来我知晓了这件事的性质,我认为能对他人做出这种事,是人类最大的罪恶,但我并不恨他们,毕竟我似乎并没有感到痛苦。
我并不敢反抗,是怕他们将这件事说出去。但我也不想反抗,因为这种事我从来没反抗过,他们并不是第一个,而第一个对我做这种事的,是所谓的“生活”——我根本无力反抗。
这件事,我不会和任何人提起,因为即使告诉了,也不会有人帮我伸冤,反倒是会使我落入无尽的深渊般的羞辱之中,我不相信那些人,因为我受他们迫害,但详情我实在是不想提起。
在随后的校园生活里,我时刻防备着他们,这使得我的神经无时无刻不是保持紧绷,保持着一脸惊恐的表情,这使得我越发得神经质。但这似乎造成了一种契机,那些人似乎觉得我这样子是故意的小丑行径,便不再与我真刀真枪的争锋相对,也似乎也不太理会我了。我发现了这一点,便开始以搞笑为生路,从而使自己不至于再受更大的伤害。
我用搞笑伪装着自己,再高超的伪装技术,也终有破灭的一天,我似乎很快就迎来了这一天,对此我是非常抗拒的,可似乎并没有什么用。
我曾经认为他们不会将那些事说出去,毕竟当时我曾经向他乞求过。
“关于那件事……你可以帮我保密吗?”
“嗯……可以。”
“谢谢!你真是个好人。”
“是吗……”
这似乎是一件好事,(我并不是没有体验过所谓美好的事物,以前或许有过,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喜悦的情感早已无法再次体会了。)但最后我才发现似乎所有人都知道了,只有我还自以为是的做着小丑。他的极不道德的行为,如同阳光灼穿了黑暗将我燃烧。我承受着无尽的痛苦,他似乎是穷追不舍,非要将我烧杀似的,我似乎是无辜的,应该是的吧……我本应该是早就知道的啊,我变得愚钝了?似乎并不是啊……是我自己不愿意承认啊,或许……不,确定,我其实早就明白了,只不过是我自己欺骗了自己,还不敢承认罢了……
自从那次事件之后,我便一直都是一幅浑浑噩噩的样子,终日饮酒,身体也每日逾下。哪怕是到了新学校,也依旧是如此。甚至是有一回,因为身体原因,在家卧床一整个学年,一节课也没上,但是却被那些不明所已的人强行拖去参加期末考,并在自己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考了全校第一的成绩。
但我对这些东西并不会在意,我能在意的似乎只有享受这一件事,但这种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吧?但我实在没什么事可以做了,我什么都做不到,那似乎是我对于光明与希望的最后的追求。我的所做所为、所想所思所带来的耻辱,使得我不得不向这可恶的世界投降。我虽然这么做,但这现实却还是无情地撕开了我脆弱的伪装,这真是可恶。我却是已遍体鳞伤,我不复不向上看,努力寻求世界的原谅。
那一段时期被我称之为“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之中,我的时光主要被享乐和创作所支配:我在享乐之余,也多会将享乐的过程记录下来。这反而使我在的一些圈子中竟然有名起来。不过,人们表面上夸赞,奉承我的作品,背地里却又是在大声地,毫不避讳地批判着我的文章。
这些我都是知道的,但我丝毫不在意他们,他们并不重要,不过是自以为是的跳梁小丑。
我为了享乐,经常是与一些闲散人员外出,多是流连于烟花之所。在那些地方,我似乎应当是发现了,那能令我暂时逃离这个世界,那些风尘女子,她们仿佛不是人类,她们应当是于世界的角落的黑暗中的生物,她们没有情绪,却总是一副笑脸挂在脸上,她们应当与我是同一种类,没有差别的,而且我也只能在她们与酒之间找到疗伤的地方。
其实我原本并不喜出门,而是蜗居在家,自己创作或是看些动漫之类。
我对于外出仍然是恐俱的。对于社交这件事,我其实并不擅长,与陌生人交流,我总是感到无所适从,哪怕是购物时结账,我仍然能因恐惧而忘记收取找头。在这一点上,我是愚蠢的,我无法想到任何一种方式去掩饰我的内心,我不净的思想就此暴露在阳光下,由世人的眼光的燃烧,我无法再进行任何的小丑行径,在世人眼中,我或是一种如猛虎的存在,令其警惕以至厌恶。
后来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不过说到与他们的初见面,却是十分可笑的,不如说这应当是我苦痛的开始,不,应当是我的心理在某种层面上吸引了他们的到来?
那次我卖书归家,因为怕人,所以走了一条小道,不料被一名匪徒强行拦下,他似乎是以为我应当是有很多钱,毕竟不管是从穿着还是样貌来看,都像是家财万贯、不事劳动之人。但他想的不太对,我身上早已无半文钱。
我流露出惶恐的神情,睁大眼睛看着他。他似乎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不太熟练,对于我的反应似乎有点出乎他的预想,他的反应也似乎是出乎我的意料。
“既然你没有钱,那,那我就送你回去吧……”
“?”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完全不像是一个劫匪能说出来的话,倒像是一个热心的路人。
他的声音越到后面就越来越小,不知是因为害羞,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看他的模样,也不过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罢了。因为戴着口罩,所以我看不清他的脸……
“你,你不说话,我应当你同意了啊……”
我似乎盯着他看了很久,他被我看着有些不自在,眼神有些回避,把头转向了别的地方。
我注意到了我的失态,也收回了目光。不过,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少年啊。
后来,我每次出门卖书,他都会送我回家,一来二去,我也和他熟络了起来。我们二人在路上聊了很多的东西,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了香烟、妓女这些东西。
他的身上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堕落”的气息,昏昏沉沉,令我欲罢不能。我遇到他,就像是落叶遇到河底的卵石,顿时黏着、缠绕在一起。我似乎是找到了一名志同道合的人,我不禁欣喜若狂。
不久,我应当是出于想与其相处更久的目的,我便请他到了我家做客。他一开始是抗拒的,是源于青春的滞涩吧,或是别的什么,我不甚明白,但他终归是同意了。
但直到现在,之前以及未来,我都会认为这是我一生所犯下的大错之一,这应是过度的感性与热情导致的不可逆的结果。或许冷漠才是人的本性,似乎只有如此,人才能称为正直,从而不受任何侵扰。
我邀请他时,家中已只剩下我一人,其他人早已移居他所。偌大的宅院之中,也只乘下我一人。对于这样的情境,我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的不适,自从他们离开,我便与他们尽量减少交流,除了每月的学费和毫不起眼的生活费之外,便几无来往。这反到为我塑造了一处绝佳的巢穴,便于我能免于阳光的灼伤。对于他们的心情,我是不想理睬的,也无法回应,我不明白人类的情感,尽管会有共情的时候,但仍是无法理解。
我把我蜗居在家时所写的文章和所做的一些杂物拿出来,请他评析,这时出于我对于他的一种莫名的信任。我对于这些画和文章,我始终认为,他们是不能被他人所知晓的,哪怕我曾经把一些诗文发表出去,但那也不过是一些媚惑之物,从来不是我的内心的表达。但他们我是从来不让他人知晓其存在的,他们一但暴露,我便将死无所归……他们似乎是绯色的吧。对我当时的行为,我至今仍然后怕,但好在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后果。
我指着一幅画说:“这幅怎么样?”
“像……你是,一只来自地狱的鸟,被关在了笼子里。”
我神色一顿,他是怎么看出来的,我并不知情,或许他真的是我的知己,是上天赐予我这个罪人的救赎吧……
他神色慌张,仿佛是说错了什么话一般,紧张的观察着我的反应,是因为羞怯吗?是的吧……
我与他又聊了许久,他与我之间的对话也逐渐多了起来,他提出说要带去一个地方,我也就答应了,我也是从那时才知晓,这世上竟有与我同类之物,我不禁泪流满面。
从那之后,他便多次带我前往那烟花之地,他身上俨然有一种老手的气质,在那种地方,他明显变得游刃有余,显然,这种地方才是他的主场。
怪哉,难道与我有想通共鸣之处的人,都是算不得人的吗?
后来,我与他便成了那里的常客,那些同行的,人们口中的“狐朋狗友”,也都是他喊来的。
自从我与他相识,他也从我这里的书上学了点权衡之术,于是便逐渐成为了周围一带闲散人员的头目。后来也是渐渐发展,似乎是已成为一方有名的势力。不过也是实在好笑,我自己并不善于与人相处,但我所写的东西,别人看了一点,就能有如此大的改变,真是怪哉。
在他成为头目之后,每当我出现在那种地方,便总是会有很多人前来向我讨好,希望和我搞好关系,从而联系上他,而且其中是以女性为大多。不过他们似乎也是对我有所图的。人们表面上仪表堂堂,实际上背地里却是放纵自己内心欲望的猛兽,人们总是用表面来掩盖,自己的内心,但似乎只要细心一点,我们便能从任何人身上找到变态的心理,哪怕是圣人或是婴儿,人类明知这一点,却故意忘却,这就是如此,世人才在理智中堕落。
我与他时常同游饮酒,这也是那些找我的依据,但他的酒品很差,酒量更差,对于这一点,我也是无可奈何的,必竟我也只是一个柔弱的人啊。
有一次,他喝醉了,红着脸问我:“你喜欢什么花?”
“桃,花。”我一字一句的回答他。
“啧。”
于是乎我便被他一脚踢出了酒馆,这也成为了酒馆的一大笑料。
在酒馆外面,我躺在雪里,我不想动,任白雪和着污水打湿我的外套,我看着天上淡淡的紫色的霞光,我似乎只能是祈望,我能被温柔似待。我想着什么,我不知道,只是有泪划过脸,脸上留一道道的霜,我沉浸在其中。
【第二章·承】完
空与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第五人格同人——盲蝶
- 简介:第五人格盲女海伦娜和红蝶美智子的甜蜜日常❤……
- 0.2万字2年前
- 异界重生之复仇
- 简介:主角朱吟乃玄武大陆的界主,因不满天神帝陵天的判决,遭众神追杀,被逼无路,跳下多贝雪山,可竟然没死,还在异界重生了,因此还保留着前世的记忆,辛苦回到了本来的世界,一场复仇之旅开始了…
- 6.3万字2年前
- 何使皆以默
- 简介: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那时温柔阳光的你一生忘不掉的你
- 0.0万字2年前
- 绝世大圣
- 简介:自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在一座直插天际的高山上,矗立着一块集天地精气所生的灵石,这一天,在高山上的灵石周围出现了一圈圈的灵气漩涡,突然一声震慑天地的巨响,一代天骄齐天大圣,横空出世,此后齐天大圣,踏万界,视万物为蝼蚁。
- 0.9万字2年前
- 一可
- 简介:让他们
- 0.7万字1年前
- 那年懵懂的我们
- 0.6万字9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