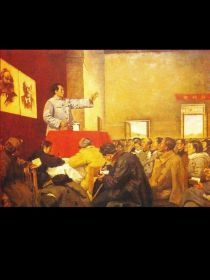第七十九章 相 离
“我的儿,你方十四岁就一个人出去打仗,你让为娘怎么放心得下哪!为娘就你一个儿,可不能出半点闪失,听为娘的话,咱们不去了,就算为娘求你了好不好?”
太子阿兄被皇后死死拽着脱不开身,只好耐心与她劝慰道:“儿此去是为巡视,不是去打仗,且儿自有主意,您莫为我忧虑……”
“你有主意?你能有什么主意!”
皇后猛然甩开阿兄拭泪的手,冷声恶狠狠地瞪我:“我儿是太子,皇帝却听你们母子二人的谗言将他支使到外藩,打得什么主意,当孤不知?待我儿死了,你这孽障可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太子是也不是?你,你就是要我儿当扶苏!”
扶苏是前朝始皇帝的大公子,因为被遣到外地而难见父亲,最后被赵高等人阴谋害死,即位的秦二世乃是他的幼弟嬴胡亥。
可我既非胡亥,阿兄也并非扶苏,此去是阿兄自个儿的主意,他与阿父奏禀要“布施德政”非去不可,莫说那些大臣劝他八百次尚且无动于衷,我将他当我的庇护拦他都来不及,又怎么像嬴胡亥那般给太子阿兄使坏呢?
总而言之我在皇后这里是没法解释清楚了。
是以皇后痛恨她的,我忙我的,我自她颤抖的指下默声低头,自腰间解下与阿父下棋赢来的龙渊剑,仔仔细细地抚了抚,再仔仔细细地佩在了阿兄的身上。
“我不晓得您为何忽然想去外头闯荡,”我将阿兄拉去一旁,仰头看着他初生零星薄须的面:“然则你既要去,无论父母长辈如何作想,阿弟我是支持的。”
到底只是十四,他这般年少稚嫩,莫说是他的母亲,就是我这个做阿弟的都不放心。
我担忧地握住了阿兄的手。
阿兄依旧改不了爱哭鼻子的毛病,与我低头对视一瞬,水汪汪的眼睛便吧嗒吧嗒溢出泪来。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的确以后是要做一国之主的呀!
断断续续的啜泣里我擦着他的眼角,口头的叮嘱不自觉多了些:“阿兄若有信陵君之志,当须广施仁德,招贤纳士,听取直谏,如此名声在外,德泽四海,针对你的阴谋诡计便会少些。只是到底出门在外,万莫放松警惕,切记防备周遭,莫让自己身涉险地……阿父那里你不要怕,你不是扶苏,我也不是胡亥,你只管做你的事,什么时候想回来了只会我一声就是,我自与阿父耳边吹吹风,他没有什么是不答应我的。”
阿兄吸吸鼻头抹了把泪,与我重重点头。
“我信你。”
他与我依依不舍地抱了一抱,许久的许久方推开了我:“后会有期。”
待最后看过我一眼,又转身朝皇后一拜。
“儿此去路远,不能侍奉近前,母亲千万照看好自己。”
“阿盈!”
太子阿兄再不看我们,毅然决然地上了车。
耳旁是妇人伤心的哭诉,金色的朝阳映着越走越远的马车,车骑旁依稀能看到周兄坚毅的背影,那一行人马不声不响地走出宫门,莫名生出一股浑然莫测的气质。
我的阿兄是要离开我了。
阿兄是想要长大。他急迫地追求着什么,我虽然无法明知,但也猜得到他不惧失去性命也要的,决非区区一个储君之位。
或许,是自由罢?
我估摸着天边翱翔的雏鹰,目送那队黑点渐渐不见,待朝阳高高挂上了天,再不愿听那宫门口妇人幽怨的呜咽,兴致缺缺地回了宫。
往后没有阿兄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阿娘不晓得我的心思,正坐于妆台前照着自个儿年轻美丽的颜色,头上戴着阿父新赐予她的金步摇,面上得意之色愈发浓郁。
“未成想不必他人多言,她那傻儿便自个儿出了宫。好如意,待阿娘好生努力努力,再在你阿父面前美言几句,不定哪日陛下便改立你为皇太子啦!”
她如是与我张扬道,激动处揽过我“吧唧”亲了一大口,头顶步摇的花朵笑出泠泠的脆响:“到时候你便做这天底下最漂亮的太子,为娘便做这天底下最漂亮的皇后,等你阿父与你传了位,也定能当个好皇帝,以后少不得给你家阿父长些脸面,为娘信你!”
真是……我家阿娘这盲目自信的毛病能不能改改。
我颇努力地笑了笑,“是也是也”地点点头附和,顺势依偎在阿娘香喷喷的怀里:“阿娘自然是天底下最最最漂亮的娘子,就像院子里盛开的牡丹花一样艳丽,像天上的明月一样高贵,世上凡俗的君王求而不得,唯有圣明的天子方能摘得,自然捧在手心里好生呵护,儿以为这世上没人能比得上您。”
阿娘听得眉眼弯弯,面色红润得宛若池塘里初露尖尖的粉嫩芙蓉: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我不由殷勤地回亲她一口,黏黏腻腻地撒起娇来:“阿娘~您今日打扮得真好看,儿方才都看痴了,儿为您奏一曲《扬荷》好不好?”
(双男主)白莲花养成记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汪汪队之乱世英雄
- 0.1万字2年前
- 三国:黄初之年雨落时
- 简介:【本文已于2021.8.16签约完成】【更新较慢,但一定不会放弃,可放心食用】标题出处:黄初八年正月雨——曹植《慰情赋》他是枭雄曹操最为宠爱的四子,名唤曹植,文采斐然。曾在铜雀之上作《登台赋》一首,也曾立志尽己所能报效国家,更是赋诗言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而他是曹操存活下来的长子,名为曹丕,更是曹植最尊重的长兄。六岁会射箭,八岁知骑射。却在十岁那年亲眼目睹昔日敬重的兄长曹昂为掩护他而死。曹丕:子建…我最大的愿望,便是你不要步为兄的后尘曹植:现在连二哥都不愿信我么?
- 12.2万字2年前
- 天帝竞争
- 简介:公元1108年,由天依国发起战争,欧德帝国建立,帝国历史第一国师图海与天依国第一皇帝瓦恶的战争排名竞争。
- 1.8万字1年前
- 中国历史之史记
- 简介:来讲一讲史记,内容有些枯燥乏味,不喜欢看的请划走
- 1.1万字12个月前
- 历史上下5000载
- 0.1万字1年前
- 重生之我有最强召唤系统
- 简介:杨凝重生了,来到了一个异世界。在这里,军阀割据,战火连天。百姓叫苦不迭。他获得了最强召唤系统。且看他如何在乱世中打下万古基业。
- 0.1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