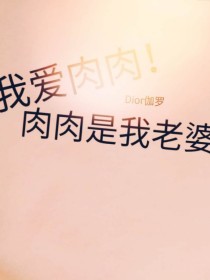40.“木偶与麋鹿。”
视野中是一面很高很高的墙,用纯白的大理石一块一块地雕砌而成,仰着头看,日光高不过墙头,在那高墙后面不甘地跳着,眯着眼睛,尖细如针尖的芒线在眨眼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刺过眼皮,闭上眼睛时,眼前尽然一片晦暗却发亮的红色。
光线越不过的高墙上,穿着银白色盔甲的守卫像戏剧中的木偶一样整齐又好笑地列成一排,那么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生计困顿的醉酒之人看了,难免要笑上几声。
他披着黑乎乎的斗篷,兜帽投下的阴影几乎将整张脸都罩住;他掏出腰间的牛皮袋,弯着手指用生了一大块老茧的骨节顶开盖子,仰起头喝上了一大口鹿血酒。
身下的麋鹿颠着蹄子,像是等不及了,他把嘴里的酒腥味连着口水一起咽下去,夹着牛皮袋子的手用力拍了几下麋鹿深色的的硬皮,低低吹了声口哨,站在城门边的士兵退步行礼,右手握成半拳,掌心向上抵住胸膛。
他大声笑起来,掐着牛皮袋的开口仰起头,浅红色的鹿血酒洒进他的喉咙。
麋鹿的硬蹄重重地砸向地面,银白色的城门为他大开——
“哈哈哈哈哈。”他举着牛皮袋大笑起来,一只手扯去身上黑色的斗篷,浅棕色长发被发带束在身后,浅红色的眼眸迎着从高墙倾泻而下的光亮,华美的服饰上,一朵殷红的玫瑰别在他的胸前;他将牛皮袋放回腰间,又在腰腹处翻翻找找,不知在哪里抽出一双白色的手套,浅笑着套在手上,来来回回地捋顺指尖细小的皱褶。
“王,斯因塞公爵已在主殿中恭候多日,”这声音在士兵之间响起来,他仍以两手交叠摩擦的方式捋着手套,眯着眼睛俯视着站在主道两侧的士兵,他找了有挺久,似乎是因为眼神不大好,直到一个绿眼睛的士兵向前走了一步。
绿眼睛的士兵单膝跪在地上。
他笑了一下:“抬头,抬头,你的眼睛很好看。”
于是那士兵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一双绿眼睛眼睛像是从蛹中孵出的玛瑙。
“哈哈哈,你叫什么名字?”他对着那士兵说话,眼神却没停在他身上,仰着头抻了个懒腰,又勾着右手的食指去拨弄胸前有些枯萎的玫瑰。
“我的名字是苏维西。”
士兵心跳如擂鼓,不停地咽着口水,半晌没等到回音,听见周围传来许多捂着嘴才能发出来的笑声,他还没回过神来,从地上站起来时,手脚抽了筋似的发麻,仍半低着头,呆呆地看着自己的佩剑。
“看呆了?”麦阿勒从后面走过来,一只手搂着他的肩膀,另一只手指向走进王城的麋鹿留在视野中的背影:“王是好看了点儿,但他是个男人——”
苏维西转过头,看见麦阿勒皱着眉对他笑,用力地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而且这儿还有问题。”
苏维西给了麦阿勒一肘击,疼痛被硬甲反弹回来不少,他沉着脸,忍着肘关节的疼痛走回自己的位置。
脑子有问题吗?
“……我没看出来。”某个新上任的士兵意外坚定地自言自语。
———
“法伯迭安•兰开斯特,兰开斯特的王,借宫宴乔装成贵族来访,借机与玛格丽特私下接头,现在已经离开了。”
加西维亚伸手拎起桌上瓷壶的壶耳,向杯中倒了一杯咖啡:“……”
瓷壶被轻轻地放回去,加西维亚侧着头打量杯中颤动的咖啡:“……我知道有个人会借此混进来,但没想到这人是那个出了名的傻子国王……”
“有意思。”
“不过也没必要这么说,相较于别悉左城里那个装傻的王,兰揭城里九个月大的婴孩登上王位,以此使他的母亲能名正言顺地通理国事,摸着祖辈的血系与他国暗中结盟,这才更为可怕,你觉得呢?”加西维亚没听到回音,只在静置的咖啡上看见自己平静的倒影。
他捏着细小的银勺搅碎咖啡表面沉淀的平静,缄默了许久后,听到敲门的声音。
加西维亚苦笑着揉上太阳穴,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尝起来不算太糟糕,但已经凉透了。
门从里面被打开,埃里克走在前面,伊卡洛斯跟着他从门外走进来,他已换上了贵族的服饰,胸前空空如也,没有红玫瑰,也没有白玫瑰。
“尊敬的加西维亚公爵,这位便是代达罗斯公爵,玛格丽特王后的兄长,雕刻花园中那座蒙纱人像的工匠之一。”
阿撒兹勒的玫瑰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往生有泪
- 简介:这是一部玄幻仙侠言情小说,里面有爱情,有亲情和友情,每一种感情都是很珍贵的,故事新奇,内容丰富,如果有错误处读者们可直接挑出来,我一定会认真看的嘻嘻。希望读者们能够坚持阅读下去,后面的故事会更加精彩哟!
- 1.1万字1年前
- 仙沄阁专用剧本(勿用)
- 0.5万字1年前
- 花谢星涵天
- 简介:她,本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可以享受世界上所有的掌声与鲜花。一场车祸,让她失去所有,从枝头跌落,沦为尘埃。她,本以为可以在孤儿院中度过美好的童年,纵使没有亲人,可有他的陪伴。一场大火,一切美好的记忆成为灰烬。再次醒来,她只有——报仇!车祸?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大火?究竟谁才是主谋?梦中频频出现的蓝衣少年,他又是谁?狂拽的富家大少,冷傲的古族家主。谁才是幼年与她一同走过的人?谁又会陪伴她到最后?千年的世仇,是否会阻挡他们的缘分?永生的诅咒,是否会破碎他们的感情?隐世古族之危,又需要她做什么?两强相争,必有一伤,是她殒还是他亡?若隐若现的身影,似梦似真的记忆,都在告诉她什么?还有什么在等待着她?
- 9.8万字1年前
- 山间的麋鹿遇繁星
- 简介:【已签约,拒绝盗版抄袭转载】一个是活了千年的傻白甜,一个是有点腹黑的小孩,本以为会有甜甜的恋爱,但是半路杀出个初恋怎么办
- 5.7万字1年前
- 他老婆是鬼后肉肉
- 简介:“喂!你知道吗,我老婆是鬼后!”“……兄弟你没发烧吧,脑子怎么样了…”“我没骗你哦!我老婆虽然是鬼后,但她可是我最爱的肉肉!”“…那照你这么说!你老婆是鬼后!那你就是鬼王咯。”“呀!恭喜你猜对了哦~”
- 2.6万字1年前
- 蛇生如此快活
- 简介:【已签约书籍,禁止转载.抄袭!】修仙界修的是道,法,天,身心与天地。其中的酸楚与汗水又有谁能知道?世人皆知糖素喜怒无常,心狠手辣。但又有谁能知道她曾经经历了什么?爱人的背叛,朋友的冷嘲热讽。就连自己最尊敬的师尊也要在背后捅自己一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灭他满门。人生为己,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 11.6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