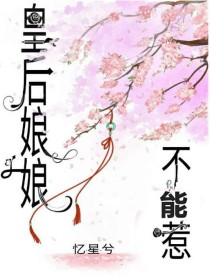第二十六章 心蛊
刘彻抚着她散下的长发,眼中满满是痛苦,道:“说哪里的话,妍儿怎会有什么不测呢?你的兄弟,孤也从未苛待过。”
眉头紧锁着,多希望抱病的不是怀中纤柔的女子,而是自己。
但李夫人一眼都不想看他,只是凄凄然地捂着自己胸口。
“奉承他,便可好过了。温柔以对,心口就不痛了。”心里总有一个声音这样告诉着她
重复喊着“陛下”二字,佯装心心念念,佯装满心满眼皆是刘彻。
多么可笑,,她已经不愿意再违背自己的心意了。
慢慢地,李夫人昏睡了过去。
深夜里,惨淡的月光迷蒙在窗外,一星半点的余晖都进不来。
“清徐,”李妍醒过来时,刘彻已经离去。
殿内飘散着些许清淡的香味,那是李延年给的安神香的味道。只是李妍日日都点着穷桑,从没有用过它。
是谁熄了香炉,点起了这安神香?
她的声音有去无回,清徐像是不在。
“要喝水吗?”耳畔传来了陌生男子的声音,李妍一惊,差点大叫。
那人赶紧捂了她的嘴,李妍这才看清,来人正是金乌。他依旧是一身黑色的长袍,坐在了她的床边。
不仔细看,真分辨不清有人在此处。
他小声的说:“别叫人,我就是来看看你。”
声音沉沉,真是好听,叫人不禁神往。李妍平复心情,望着他,点了点头。
金乌这才慢慢地放下了手,眼眶被她全部占据。李妍被他瞧的有些紧张,撇开了头。
不知何时,迷离的月色悄然而至,透过帷帐落在她的身上。
“你……”她想开口说些什么,却是不知如何说下去。
他倏而笑了,抚摸着她未添珠翠的长发,然后为她奉上了茶水。李妍不作声,只是默默地接下了杯子。
她饮过茶水,偷偷瞧了一眼金乌。在他眼中仿佛捕捉到了些许悲凉,她不觉得诧异,反觉得似曾相识。
“近日抱恙,不想想原因吗?”月光映在他的眼眸里宛若清泓。
“都说了,我是无玉之命。连日来带着那玉簪,可不是要心痛难耐了吗?”李妍自嘲着笑了笑,又指着案几上的香炉,“可否帮我点上,我不要闻这安神香。”
金乌走到案旁为她重新点香,略作了思索,说道:“这是谁给的?”
李妍靠在床头,有些头昏脑胀,回应他道:“是我哥哥,平日里我常点从你那带来的鸟型香炉。偶有几次起夜,闻到的是这安神香。”
鸟型青铜香炉重新燃起,轻烟弥漫。
金乌睨了一眼李妍,随即问道:“你的吃食起居都是何人照顾的?”
“清徐。从前跟在哥哥身边的丫头。”
金乌看着香炉青烟升起,叹了口气说:“你身体虚弱,频频无力确是簪玉所致的没有错,但却不会让你心痛。”
李妍看着他的背影,紧锁眉头着,不明所以。他拿起旁边的香炉闻了闻,冷声道:“这香可不是普通的香料。”
“哦?是什么?”心里一阵阵寒,有些畏怯,却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
“这是安抚心蛊的迷香。”他装作平静的说道,眼中却满满的阴厉。
“心蛊?”她念叨着,有些难以接受,“你是说,我中了蛊毒?”
“这蛊虽不会毙命,但下蛊的人都够暗示受蛊人的一言一行,若是受蛊者稍有违背的倾向便是钻心之痛。这迷香能让蛊虫更好的控制,也能让受蛊之人更加服从。”他将香炉丢在案上,回身看向李妍,“只怕,你在入宫之前就已经中蛊了。”
李妍呆坐着,说不出一句话来。她知道皇后没有这个能耐可以给她下蛊,既是入宫前,那么,唯一能够近身,又没有防备的,便是只有……
“哥哥竟这样对我……”两行清泪,无奈无言,让人不知如何面对。
她忽然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最信任的人竟也把自己算计的体无完肤。
争宠,夺势,陷害,算计,这些究竟是自己的恶毒还是蛊毒的控制,她不敢去认真的想,生怕那些事真的是出自自己的真心。
鼻尖有些酸楚,喉间也干涩非常。她不想哭出声来,寂静的夜里,半点声音都是如雷一般。攥紧了被褥,咬紧了牙关,却控制不住的泪水肆流。
月亮似乎被云层掩盖,四下里都没有了光亮。李妍忽然摒住了呼吸,她感觉到异样的气息离自己很近。
在这样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他拥着李妍,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安抚道:“别哭了。”
金乌的话语总叫人安心,让人愿意把自己交给他。
“给你的玉玦可还在吗?”
李妍点了点头。
“只是命中不可碰玉,便并未放在身上。”
他叹了口气,告诉她:“你哥哥的筹谋狠毒非常,若你不惜得下一世还苦苦纠缠着,就将玉玦摔个粉碎吧。”
李妍早已泪眼迷蒙,抑着哭腔说道:“摔了;会如何?下一世,就不会痛苦了吗?”
“我也不知,兴许是快乐的,兴许是悲哀的。但总不会受制于人了。”他讲李妍拥得更紧,生怕失去一般。
不知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恍惚做了个长长的梦。梦里有座高台,里头有个女人日日夜夜的看着天上的大雁。
半梦半醒间似乎听到了“子规”二字,这是梦中人的名字吗?
总有一个身着黑袍的人来到此处,不发一言,却温柔得看着自己。
自己?
若非梦中人就是自己吗?那人的脸似乎是和金乌一模一样的。
金乌……
她醒来的时候,外面日头正旺。筋骨仿佛都不是自己的,酸楚难捱,纤细的手臂撑起腰肢,吃力地起身喊道:“清徐!清徐!”
清徐赶忙进来,听候吩咐。
李夫人抬起下颚,轻蔑道。“清徐,你记着,这蛊是皇后娘娘下的。”她对清徐,再不似从前那般关切,温和。
清徐一惊,忙跪下谢罪:“夫人,奴婢……奴婢……”
这丫头还小,随李妍入宫时不过十三。过了这几个年头,也越发出落得水灵。原本李妍待她能算是半个姐妹,只是如今,夫人的这一言,当如何面对呢?
本是试探些许,李妍心中还存着侥幸,可见了清徐这般此地无银的慌张神态,什么都明白了。
李夫人急火攻心,气得直把枕头扔向她。扬起手就要挥去,如同泼妇一般。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不争,便要死,便要亡。争了,家族门楣,无限荣光,在没有人欺辱。
而她,就是华耀的祭品。
只得慢慢的收回了手,跪在地上的清徐见夫人没有落掌,稍稍松了口气,可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地簌簌落下。
李妍痴痴地望着几案上的鸟形香炉,木讷地说道:“记住了,本宫中的蛊毒,是皇后下的。”
事已至此,只能颠倒黑白。
清徐低着头逝去了眼泪,只讪讪地回了一句:“诺。”
中宫殿内,暖漆椒墙是显圣德恩宠,却只有高高而坐的逐渐色衰皇后,徒有一副空架子。
夫人美人的,穿戴花艳,叽叽喳喳的来到椒房殿向皇后请安。
软软糯糯的声音此起彼伏,佯装着毕恭毕敬,也无非是说一些好听的场面话。皇后听厌了,便挥手示意她们入座暂息。
梁美人席子还未坐热,便起身说:“皇后娘娘,我等日日都来向娘娘请安。那猗兰殿的李氏何德何能,频称抱恙就不来请安,都一个多月了,夏天都快过去了!”
一个个花一样的美人低着头都没有动作,身居高位的皇后也只是自顾自喝着茶。梁美人见没有人作声,面露尴尬神色,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一旁的王夫人便出来打圆场:“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听闻李夫人这病确实严重,来势汹汹,昨日竟是呕血了。”
皇后放下手中的茶盏,与几案碰出清脆声响,这才开口道:“罢了,不必多说了。妹妹她抱病在身,不来请安也无妨,左不过是来嚼嚼舌根罢了。”
此话一落,一众妃嫔均是跪下谢罪:“妾等不敢。”那梁美人更是将头低下又低下。
“今日且散了吧,本宫乏了。”寥寥数语便将威仪尽显,压得殿下众人不敢再有只字片语。身后的侍婢寒寄上前,扶了卫皇后入了内殿。
那些大的娘娘,小的姬妾便悻悻而去。
永巷里的女人永远都有斗不完的事,这是一场圈地自禁的没有硝烟战争。但胜利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是皇帝的恩宠,还是无上权位?谁也说不清,也没有办法解释。争斗,就这样开始,无止境的,无休止的。
不是祭祀欢庆,自不用着那朝服。可是头顶步摇坠坠,压的她喘不来气。
“寒寄,李夫人病了多久了?”卫皇后问道。
寒寄卑躬屈膝地扶着她步入内室,回复说:“想来,约莫有一个半月了。”
她坐了下来,撑在凭几上,微合双眸,凝着眉头想是相当不悦。“病了这许久,皇上几乎是日日去她那里,她还生生将皇上赶出来。”
话梦青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整个修真界都在虐我
- 简介:替身,刨金丹,赶出师门父子相认,不闻不问天降天罚,被迫献祭冰封七百年,虚境遇奉擎性情大变,状若疯狂,心狠手辣
- 1.3万字2年前
- 皇后娘娘不能惹
- 简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她,如何走上巅峰?
- 1.2万字2年前
- 宫株
- 简介:【已完结】苏柳儿本是掖庭宫最低贱的宫女,因被锦贵人纳入贴身宫女她一心想服侍主子,但直到她被皇上看中成了后宫嫔妃,野心就冒出来,陷害淑妃没成功被禁足后还是洗白,从宫女到皇贵妃再到太后,最终成为了皇帝最宠爱的美人,这其中的过程如果说不复杂的话,那真的是骗鬼。但是现在,苏柳儿已经不是那个掖庭宫最低贱的宫女了,而是皇贵妃最宠爱的嫔妃。
- 28.6万字2年前
- 与终离
- 简介:我是一只出生在庚古天天喝着露水吃着灵草园里的各种灵草长大的兔子,唯一的想法呢就是无忧无虑的活着天不遂人愿,百草园被毁了,庚古的各种动物死的死伤的伤,自己受了伤灵力受损,就连阿姐也被惨杀,这世间又剩下了阿怀一人。烧杀抢掠只为了一颗草药!“就是你杀了阿姐毁了庚古,我要为他们报仇!”
- 0.3万字2年前
- 溺宠三千,废柴二小姐
- 简介:神为21世纪第一杀手,居然自爆而死!但好在老天待她不薄,让她重生于西霄大陆。绝艳清华之貌,可惜却是一个废柴。到如今本小姐来了,废柴?到底看看谁是废柴。莫名被逼婚五王爷,但是为什么明明名花有主了却总有些人倒贴上来,大婚当日,当街四顶花轿前来拦路,眼下之意,先逃为妙
- 0.3万字1年前
- 穿越误惹高冷王爷
- 简介:特工杀手穿越古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本以为可以笑看天下,却被冷王缠身,且看她如何开启新的人生
- 0.0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