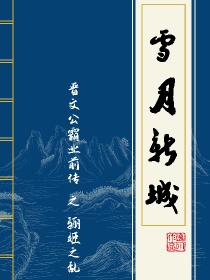第三十七章 侄女
一年十二月三百六十余日,我虽说与阿兄也算朝里朝外数一数二地亲近,然则其实能一起相处的日时日非常有限,就说是去岁到今年元月,除却日常的三日一朝和必要的大朝,一月至多也就五六次私下相会,属实算不上太多。
新年刚过,少府监已开始开工,我就着送来的各尺挨个校准着,木工尺、衣工尺、市尺……我生来便对这些度量类的敏锐些,只对着这些尺这么一看,便能轻松分辨出其中优劣来。
“有话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放下最后一尺拍去手上的尘土,看向趴在案上同是认真观尺的尫娘:“工匠遵循成规不够,还需尺准而精,方能制成可用的工器,上好的工器配上上好的料,方能制成上好的器物,这里头的每一环节都甚为重要。”
说到大兄家的这二娘子,今岁也不过八龄,人也生得瘦瘦弱弱的不大康健,然则大约也正是因这身子,心思也比旁的孩子沉静,去岁偶然的某日我替她和十一娘开解了一个九连环的玩具后,就时常借口跑来我这处寻我玩了。
她似乎沉溺于那尺里,黑漆漆的眼眸映着手中木尺的刻度,眉眼沉静如水,带了那么几分和他父亲相似的神采。
我话已毕,她方不紧不慢地放下尺冲我眨眨目:“儿比照一番,这尺是最好的。”
二侄女眼神真不错,这尺恰好是我亲手刻的。
我正欲夸夸我这聪明可爱的侄女,再与她传授一些我最近算经所得,不知哪儿听来风声的十一娘风风火火而来,“姊姊姊姊”地招手喊向这方,身后的几个仆从追都追不上。
天,这孩子大雪天地跑甚,给滑倒了怎么办?
还好我这乌鸦嘴没打算开口,那红团儿球方有惊无险地跑了来,还未站定,看也不看我就拉着二娘子拉着人就走:“耶,我带姊姊去和阿妹们玩了,您自己忙。”
“……慢着点走!”
我当然不能和小孩子抢玩伴,心惊肉跳地看着那一白一红两个团子拉拉扯扯地不见踪影,无可奈何轻叹一声,传人将择好的尺送回各庄。
这二侄女是我见过几个孩子里资质极好的,可惜身子不大好,不然也能当学徒教养。
这般打算着,室外的笑闹声还没停下来,又有熟人来访。
“阿劼?阿劼最近不来我处,可在忙什么呢?”
听声音自然是我亲爱的大兄。
门外俊朗的男子先是探进一颗脑袋,入内后脱却一身厚厚的貂裘,坐下身笑融融问我:“五日不见,可有想我?”
我一时未答,视线落到他不自觉覆住的胳膊上,眉心微皱。
“这几日天冷,你怎么……”
我欲言又止,对方疑惑地眨巴眨巴眼,一脸地清纯加无辜。
好吧,他长的腿,又没人能管住他,自然想来就来了。
我只好咬牙让人再添了两个火炉,殿里温度上来又打了盆热水,好生给他捂了会儿胳膊,那被冷天冻得素白的脸上方回了点血色。
“阿兄每年来我这里,总是尤其地费碳,”我执着被下略冰的手放于心口,那处痛得滴血:“很费钱很费钱的。”
我神色已算得上狰狞,阿兄也只是揉揉我纠结的眉毛舒朗一笑:“我相信阿劼养得起我。”
论强词夺理我自然比不过厚脸皮的阿兄,今日注定是费碳的一天,我只好顺势轻笑地随他窝在一处,听着外头树枝折断的咔咔声,炉火暖烘烘地烧着,什么也不必多说,什么也不必多想。
“我大约是年纪大了,”大兄亲了我脸颊一口,些微落寞地枕回我的胸膛:“最近总是想起过去的事。阿娘,阿妹还有阿弟……那时候亲戚们多好哪,而现在做了什么皇帝,却也失去了太多,论起舒心自在不比从前得多呢。”
生逢乱世,哪由得人想不想呢?
我抚着阿兄完好无损的脖颈,心下的某处一疼。
都是鬼门关捡来的命,能活着就已是老天赐福了,更莫说还九死一生地做了皇帝,更是不知道拿自己的脑袋做了几次赌,没什么可在意的了。
然则阿兄不类我这般冷血,他是正常人,他知道害怕,知道恐惧,也知道为成就这份帝业牺牲了多少的命,现下的落寞也不过是正常人该有的发泄,也是拥有良知的正常人该有的表现。
若是生在太平年间,他也该是好生生地当着他的国公世子,或是为朝廷出将入相的罢。
可惜没有如果。
天黑了下来,室内又冷了一层,炉内的碳被我支使着人再添两铲,热气上来,怀里的人也熏得阖目昏睡而去。
李建成x李元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尘灰间的天兰
- 简介:1950年,人类与侵入地球的异族开战。持续几十年的战争,使人类丢失了全球80%的土地与大部分人口。1981年,仅存的人类聚集在几片仅存的土地,继续同异族对峙。7月,边境城市‘畿平’遭到异族的攻击,即将沦陷。被困市区,未能及时撤离的高中生——卫远平,在危急关头,被两名神秘的少女救出。而接下来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事件,则将他一点点的拉入了一个惊天的阴谋漩涡……
- 2.4万字2年前
- 记鱼汤史
- 简介:在无尽的MC大陆上,鱼汤之国的历史
- 0.4万字2年前
- 时空穿越:大宋
- 简介:当时空穿越来到大宋朝,看尚方信、梁山好汉和大宋之间的风云故事……
- 4.9万字1年前
- 雪月新城:桓庄之族的覆灭
- 简介: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五千年风华烟雨,是非成败转头空!春秋初年,曲沃代翼尘埃刚刚落定,晋献公初登君位执掌权柄,处处受到公族的掣肘制衡,君臣之间互相角力,一场残酷的宗族内斗呼之欲出……本书是《雪月新城》系列的第一部:桓庄之族的覆灭。
- 4.9万字1年前
- 盛世浮华:情殇绝恋
- 简介:谁能一诺情长,谁又能一世相守?我们只是用了彼此认为对对方好的的方式对待彼此,却不知这或许并不是彼此想要的。从而错过一世,也殇了一生。用一世情殇换你十年迷离。盛世浮华,十年相思,百年渡。
- 0.5万字1年前
- 蛟龙小队——滨海城之战
- 简介:在1个月后,蛟龙小队来到了滨海城。那里,有一个狙击组织,名为“蜘蛛”组织。他们个个是狙击高手。那么,狙击高手与狙击高手碰撞会怎么样呢?
- 4.8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