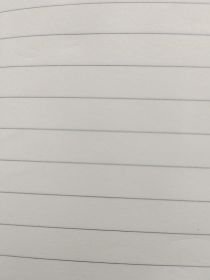31.医生,我看病
我是一名精神病医生,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精神分析科。回国以后听说精神科医生的工资会比其他科多几块,这个钱被戏称“挨打费”。
好多精神科医生有过被患者打的经历,我曾经也被踹过一脚。
有一天,下午快下班了,听到一个人在走廊里大喊,谁是刘方宗?!
我赶紧出去,只是出去看看情况,没敢承认是我,因为他一直大声喊着:“刘方宗出来,我要把你崩了!”
我正在寻思自己最近接过哪些患者,是哪里得罪了他。
他自己说出了原因:他是别的病房的患者。在那个科主任查房的时候说睡眠不好,给他请一下心理科会诊。当然那个科的老师不敢跟本人提精神病这件事,避重就轻的说睡眠不好。
于是他就记住了,没等到我去,他就自己打听到我的名字,要来把我崩了。我跟他解释说,我还没有收到会诊单。从主任说会诊到管床大夫递单子到物流送过来到我过去是有时差的。
周围的患者和同事也在帮忙解释,但是他暴跳如雷,哪可能听我的解释,一直在骂。那种说话的密度是不可能插上嘴的。
长期在精神科训练的本能,让我一直和他保持着距离,并且在心里盘算如果他向我扑过来我要怎么跑。我们办公室有两扇门,窗户也是打开的,我是从窗户跳到阳台快还是从另外那扇门跑更快。
这时他儿子来了,他骂我骂得正起劲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他儿子,嘎然而止,立刻转向他儿子,“你给我买的高血压药呢?”
他儿子没理他,“你在这里闹什么?”
然后要拉他走。一边走一边道歉。
他揪住他儿子的衣领骂,“你个B崽子!”
又是一顿大骂。骂着骂着,不知道想起来什么,就走了……没有任何解释,直接就走掉了。
接着我的门诊门口出现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挂号单,脸上带着倦意,黑眼圈很重,皮肤却很白嫩,看起来很像蒲松龄笔下被鬼怪吸了精元的书生。
他好像已经站在那里看了好久,看我发现了他,于是向我挥舞挂号单,“医生,我看病。”
在精神科很少遇到年轻人,以前更少,现在因为社会压力太大慢慢上涨了些,但来的年轻人大多都有家属陪伴。他是一个人来的,就很奇怪。
“你觉得你哪里有毛病?”
他笑着向我指指脑子。
“有什么以往的病史吗?”
“我爸是疯子。”
李陆生,95后,曾经在旅行社实习一年,后转攻摄影行业。父亲是北大高材生,那个年代读个大学不容易,我不觉得会是疯子,母亲是电厂职工,后来辗转多地打工。
小时候经历过创伤,既不内向也不外向。从业四年,做过摄影师,门市销售也做过修图师,但是都没做长久。学过华尔兹,英语专业六级,德语专业四级,私生活混乱,曾经怀疑自己脑子里有寄生虫。
李陆生没告诉我他失眠,但是我感觉他一直睡得不好,眼神中透露着清冷的气息。我接触到他,是因为他和我的雇主有关系。
“你不是在江家做私人医生吗?我们做笔交易,你对我来看病的事情保密,我就不会告诉江家你接私活。”
我把放在屁股下面的手抽了出来,正襟危坐。他要是没有精神病,就是个偏执狂;要是有精神病,那就危险了。我桌子上专门放了一个按钮,遇到危险一按就可以连通警卫的对讲机。
牧羊少年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换身妻子
- 简介:感到婚后无聊的我在一个夜晚遇见醉倒在路边的性感美女,却无意间身体交换了,变身美女的我偶然间发现了交换的秘密,随后计划将美女与妻子交换,想着过上风流生活,殊不知一切正在悄然变化着...
- 0.7万字1年前
- 负光
- 简介:另一条时间线
- 1.4万字11个月前
- 都市反派,我抢走男主后宫
- 简介:一次偶然,苏北穿越到了某本爽文小说里,并成为了女主李若冰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男主很快就要找上李若冰,这不行,吴辰这个渣男,配得上我们老板吗?既然已经穿越了,看苏北如何截胡李若冰等女主,调打吴辰,我的穿越之旅,从强吻李若冰开始(封面是李若冰)
- 0.0万字12个月前
- 匆匆遇见你
- 简介:暗恋是一种美,遇见你,心却跳动不止,这就叫做真心地喜欢。
- 0.2万字1年前
- 王俊凯之我走了
- 0.3万字11个月前
- 在QQ上装男生
- 简介:一点也不腐,这是我灵感突发写的作品,不怎么好,请大家多多见谅本文由现实改编
- 0.3万字1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