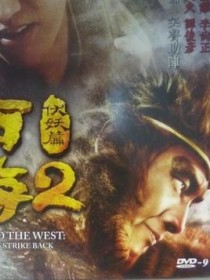八、如今可理解了几分?【卷一、六界续书】
“是《六界全书》!”花千骨压低声音,压不住惊慌。来得如何这样快?
“明日去茅山。”白子画点头,语声持平如水,不见水中风浪或平静。让小骨定神,让自己定神。
断念稳稳落于绝情殿,二人径直去了书房。《六界全书》并无异样,片刻前却分明笼在微薄的黄光中。微光似乎只向内。只是他和小骨看到了。
“师父,为何会……”花千骨想问为何这书会发生变化,难不成是清虚道长一早就施了法?当然,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想着想着,话只说了一半。
白子画却听得明白。能回答的,却只是她这个不最重要因而在半途遗失的问题。
“这是一种法术。法术显现的时间应是在你魂魄健全后。”
这个回答,小骨想必也预料到了,还是把惊讶全写在脸上。他又何尝不是?这位在妖神大劫前就撒手人寰的老者,慈悲和智慧却留存到劫后,为六界也为他们二人指引前路。
前路。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他受清虚道长托付的当初。当年清虚道长有所预见,却不能全说出;如今他有所经历,但也不能断定未来。也如一幅画,落笔之初,不知全局,如今也远远未完成。他愈发感到修仙至今日,并未修成。只是比无念无憾的起点,多了一些理解,也多出一些困扰……
看着眼前的小骨,惊忧之浪,都在对他的全然依赖和一心敬慕的河道里,安然流淌。还是那个孩子,又回到他身边。莫名而安。她眼底的相信,如何轻易也让他相信了:重新开始,总要教好小骨。虽然小骨是个难教的好孩子,而他这个师父,也有好多不懂不会。
“现下还早,随为师去趟销魂殿。”不可以先慌乱了。
“噢,是去拜谢师叔……”花千骨吐吐舌头,一时不见了《六界续书》费解的光暗,下界时光中的“爹爹”和仙山这位师叔的形象奇异地交汇……
她依旧不能解。三尊她都怕,各有其怕。师父是太完美无瑕,在师父前,她总感到自己有错,这种怕几乎是天生天然,没有什么缘由,无法不怕;师伯的世界有太多规则,她总是格格不入,总是不能让师伯满意;至于师叔,她都说不出为何怕,师叔的世界,是另一个她不会理解的世界,不像师父那里对错分明,师伯那里喜憎分明……她不理解,不敢去窥探,也不想去。
可是,下界十六年里傻傻的自己,给这个“爹爹”添了多少麻烦!不敢想象。
两人上了断念。
“师父,不然我自己御剑吧?”花千骨小声说。以师叔的个性,见两人共乘一剑,免不了要拿来打趣……不敢想象,无奈清晰浮现那个笑容。花千骨一直就怕这个似笑非笑的眼神,比起世尊凶神恶煞般的严苛,儒尊更让她摸不着头脑。在癸班上课时被桃翁拖去见三尊,她就领教过了。之后许多年这位师叔倒不曾为难过她,却难说她少了一些惧怕。最重要是,下界这十六年……师叔是最怕麻烦的人了,恐怕他两个弟子也从未给他添过这许多乱!
琢磨间,兀见横霜剑敛着寒光,月色顷刻泠冽,冰凌刺心透骨。一阵瑟缩,耳目塞满当年瑶池惧极之下的死寂,周遭抑或心口骤然冷却,凝固了师父当年穿心一剑,还有永不敢直视的凌厉……还未全然冰冻,感到手中握住生痛的小小宫铃,是她全部所有。
白子画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大恸,——是她心口的位置,曾经藏着她的宫铃,曾经碎了她的心……可是,你想着哪怕被师父的剑碎了心,也不能碎了你我的信物?
想抱住她,用身躯为她的记忆取暖。却为她眼中坚冰冻住,长剑落地,冰碎扎心。那日刺了第二剑,只想将她抱在怀中,却又如何再去抱住这个受伤的孩子?还是个孩子,他却这般残忍!伤她这样重,再用什么抚慰?今日也不能……慢慢伸出的手终于使上气力,紧紧抓住她护着宫铃的手。他仅是比小骨更能稳住气息。往事已逝去,心境却淹留。小骨难于走出,当然不怪小骨。伤小骨的是他,带小骨走出,也当是他。不然如何做这个师父?
语声已近平静:“小骨,你可相信师父?”
“相……相信。”花千骨极力从刺向她的横霜幻影里挣脱,不断从师父赐她的宫铃汲取力量。听到师父说话,可师父的温和坚定还不能凿破瑶池当日坚冰。师父问什么?她相信师父么?这个问题她知道的,当然知道,一直知道。她相信,但她不明白……当年何至于此?如今何必想起?
“瑶池最后那一剑……”这许多年都不提,直到昨日。白子画终归认为,这一切应当解释。实在难于出口:难道不是他本意,就可脱其咎?
“师父,你不要……”穿心那一剑痛还是不痛,早不知觉了。瑶池上东方惨死,小月危亡,仙魔大战,都在师父的血迹和坠落中不见:惟独知道,是自己冲破师父封印累得师父受了伤,一念去扶……眼下也只有一念,就怕师父伤口复发!
果然见师父衣袖微动,弦音未兴琴身已颤,以她的修为都看出师父在致力调匀气息。不见流血,但眼中痛色,难道瞒得过她?
“师父,你做的一切都有道理!小骨知道,师父是想保护我的,只是我过犯太大……小骨求你了,不要再想这些了!”顺着滂沱泪水,跪倒在地。瑶池幻影已破,如何看得下师父受苦?她岂可为早已修复的伤口无病呻吟?何况她咎由自取,师父何错之有!再抬起头来看师父,已然无比坚定,“师父不答应小骨,小骨就不起来!”
小骨泪水也和恳求一样坚硬有声,刺痛了白子画。他知道这个孩子,倔强中最倔强的时刻,是为了他。小骨啊,你只想师父伤口再无伤痛,只顾回避记忆的苦楚,但这绝非长久之道。
不是才和你梳理了过往么?也是和自己……不敢进入过往,如何能应对将来?
白子画已清晰预感到,新的劫难不仅又将他们与更大的世界联系起来,还和他们自身的心结密切相关。
云山的那些日子,小骨没有记忆,记忆的血水深黑压得她苦弱不堪;从云山回到绝情殿,小骨有了记忆,为恢复记忆不得不落得五识不全。这许多年岁,都在治身治心。苦楚已然太多,无力再解释过往;苦楚已然太多,只望抛开过往悲伤,未来的日子能无忧无虑。无忧无虑不曾有过,却幻想能在未来长久拥有,这却只是幻想。过去有忧,当下有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思之长远的岂止未来?今日幸福不易,忘记过去苦楚岂不是背叛?走到今日,来路洒满心血,许以恩慈,终留过犯遗憾,不看清来路如何寻得去路?
记忆深痛,深处是生命之源。时日相连,生命一体,只因记忆,贯穿一线。心之浅表,扎不下安实之根。既已发生,必是应当遭遇,启示总面向将来。是要记住痛苦,是要直面困境。
他们从来未将过往真正谈开。从小骨偷神器离开绝情殿,一切身心苦楚都在各自承受。应说,他和小骨从不曾交流,都如最初小骨在他身边的七年,小骨是孩子,和孩子不能言无不尽;他是长辈,和长辈不能无话不说。小骨,你当成长。这是自然之道,亦是应劫之道。你要和师父一起走未来的路,我们是……同路人。
他要先学会和小骨解释。
白子画蹲下身,牢牢抱住她的颤抖,把她的心贴近自己的心:“最后那一剑,我是中了幻术。对不起……”
分不清,是师父的心跳,还是自己的。想抬头看师父,但师父抱得太紧。听到师父说话,直从心中流出,直进入她心中。不是听到,是感到,师父字字吃力,惟独借着心跳,单调,有力。到底还有多少,师父默默承受着……
“师父,还有多少?”声音仿佛是因胸中气郁,流溢出来,而非花千骨自己说出。师父终于放松她些许,她抬头望着师父的眼睛摇头。不是的,她的心痛和愧疚,总应比师父眼中的更多。
妖神出世,狠心说要和师父恩断义绝,仿佛理直气壮,实则根本没有这个资格。师父所做的一切,都不在伤害她。她全不知晓全不懂得,负了师父深恩大义,却引得师父苦痛自责!
白子画不语,小骨实实看着他,费力抬着的头坚持要师父一个回答,泪水滴落,毫不退让。你是对抗过师父,不甘心那些不公正的惩罚。可你最大的对抗,却是不让师父受伤,为此你对抗师父的道,也对抗世人之道,对抗天道。
把这个执拗抬着、看向自己的小脑袋按回怀中。
“第一剑是我。”白子画不待怀中的小骨有任何动作,接连着说,“当时你师叔要我和你解释,我说你不会理解。你不知世间往复而不消失,只不能忍受身边人的离去。而妖神集善恶一体,必毁其真身,才能引其向善一面再入轮回。师父如今和你这么说,你能明白么?”
在师父怀中不能动,熟悉的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从师父坚实的怀中传来,包围了她,置换了瑶池上不容情的目光和剑光,和她心中口上忤逆师父的惧怕与无奈。
原来如此!所以她能看到完好的小月,师父早已安排妥当。而自己那时一心和师父对抗……师父没有解释。但若解释,她真能理解?
即便放到现在,花千骨见失去的人又回来,师父说的是对的。但如何能割舍一个人,即便清楚他总有一天会回来?那时不也是物是人非?何况能否回来,谁又有十足把握?眼前一直在的,才真真切切……虽然墨冰仙也说过,只要真正珍惜,即便不是以往的形态……
可是……猛然想到那时拼命要为师父解毒,明知走上这条路,师父要如何痛心疾首……难道能眼看着师父离去,告慰自己,他会回来吗?
师父无法解释,无法纵容,只有强制和惩罚。师父做得都不错,但她却如何能做对?
“师父……”花千骨不能回答。此刻去了担忧,心头纷乱更甚当年。
白子画摸摸她的头,扶她起来,柔声化去她的千言难言:“时候不早了,我们去看你师叔。”
他哪里不知小骨心里想什么?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轻信于人,以德报怨,拼死要保护身边每一个人,虽然生命来去自有天意,祸福为报总依天理……这一直就是小骨的可爱可贵之处,也是她致命的弱点。
这,也快成了他的软肋:他再不能见小骨受到任何伤害!
也罢,他们一时也不能明悟。来日方长,且待修行。
花千骨之半缘修道半缘君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综影视:妹妹她娇媚动人
- 简介:【沉香如屑】玄夜[已完结]001-044【卿卿日常】尹峥[已完结]045-113【星落凝成糖】少典有琴[更新中]114-
- 16.4万字2年前
- 综影视明仪
- 25.3万字2年前
- 查理九世之甜蜜之恋
- 简介:过了几年后,DODO冒险队他们正处于在一个同性恋的时代,会发生点什么事呢?
- 0.3万字2年前
- 斗神降世
- 简介:斗一同人,开后宫
- 17.9万字2年前
- 芈月传—驷月情
- 简介:芈月传秦王嬴驷&芈月。高举驷月大旗!驷月同人文甜向~故事从芈月为了救弟弟小冉无奈前往承明殿侍寝开始!lft同步更新
- 11.7万字1年前
- 穿越西游伏妖篇之悟空和娜美的恋爱
- 简介:悟空,你放心,以后有我在,你那个笨秃驴师傅永远都不会再敢欺负你了——歌娜美小娜,我能遇到你,是我一生一世的幸运——孙悟空
- 1.4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