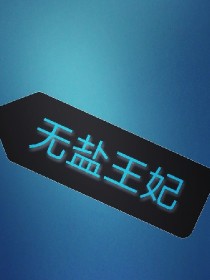06 归来痴
武冶三年,阳春三月,永安城内,中侍郎赵沿的府上发生了件奇事。
幸而,赵沿官位不高,素来行事低调。再者,赵府的当家主母吴氏管家甚严,她严词勒令,府中若有人敢乱传,便交由人伢子领去发卖处置,为此,府中的家仆婢女无人敢乱议此事,外人更是不知此事。
三日前,赵沿收到一封故人托来的密信。他面色沉重地在书房中思量良久,踌躇再三,最终在叹息中做出了决定。
他来到夫人吴氏的房中,屏退众人,扶着她的肩,告知她一往事。
他早些年间,在抚州一带认识一个女子,与其有过一段情缘,后来,二人感情淡去,那女子也离开了抚州。
分别三年后,她再次见他,称她有了他的骨肉。
此事也是在他意料之外,此时,他已然成家,一时不知作何反应。
那女子竟坦言称自己一直在外经商,无意与任何男子成家,一人也抚养得起这孩子,告知他,只是希望他能在日后自己不在之时照料这孩子,她希望他知道这孩子的存在,每年通上几封书信,此外再无所求。
他犹豫再三,最终应允她。
如今,那女子已经逝去,留下那女孩子一人在抚州孤苦无依,身边只有一个仆妇照料,他必要把她接回府中照料,已派人去了抚州。
眼下,他要吴氏即刻派人收拾一处院子来,并打点好下面的人,让他们不要在这女孩子来了后乱传乱言。
吴氏听完他的话,心中又惊又怒,当下气昏过去,倒在赵沿怀里,唬得他额上冷汗直冒。
平竹院里,苏醒后的吴氏脸色冷得吓人,她眼里带着讽刺,靠在榻上,不去看身边的赵沿。
赵沿沉下脸来,“夫人,这虽是我的错,可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都是数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们还未相识,我与那人也不过露水姻缘,谁曾想…… 如今无论你怎么想,那孩子一定要接回府中。”
“好,好,你如今是个有头有脸的官老爷了,说什么就是什么,这赵府的事是你做的了主,我不过一个妇人,哪里能左右你?”
“只是我为这个家操劳了这么些年,竟不知你竟这般……,哼,只叹我的命实在苦,哎哟!”
说罢,吴氏按着额角,头痛欲裂。
赵沿见状,脸色发青,低声道,“有些事啊,不提更好,我也是没办法。”
吴氏听了,更觉心中气闷,但她又是个性情温顺的妇人,一时气噎无言。
赵沿看了看吴氏,小心翼翼地说,“夫人,等她们来了府上,还请你多多费心,那孩子只十四岁,来了永安后只怕不太习惯,行事鲁莽,还得你这个嫡母多加教导。”
吴氏听了,冷笑数声,“你三言两语间,我便多了个女儿,只是,对外,你怎么讲去?”
赵沿愧疚地对吴氏说,“对外,就说她是元舞的女儿吧。”
吴氏抬起眼来,似笑非笑地看着赵沿,他轻轻皱眉,扭过脸去。
她忽而眼中发酸,泪水不由滴到手背上。
“我当初怎么就死乞白赖地求着嫁给你了?” 吴氏哽咽出声。
赵沿的神色愈加难堪,他在吴氏榻旁坐下,把她揽入怀中,喃喃自语,“璧儿,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
十日后,抚州城外,两辆马车正在缓缓行驶,马车前后拥着十几个骑马的护卫。
两辆马车一前一后,前面那辆简单素朴,里面坐着赵府的仆婢,后面那辆稍显华美,里面坐着赵府刚接到的二小姐和照料她多年的如娘。
此刻,如娘愁容满面,她望着昏睡中的令徽,悲从中来,这孩子不久前没了娘,日日伤心。
五日前,她发了高热,昏睡过去,呓语连连,不断喊心口痛,把她吓坏了,请郎中来瞧,也看不出患了什么病,只说伤心过度而致心悸,想必无大碍。
幸而,她两日前已经醒过一回,才能跟着前来接人的赵府众人动身,只是一路上人都昏昏沉沉的。
一个时辰后,令徽醒了过来,她倦怠地打着呵欠,不知为何,她觉得自己好累,在梦里,她好像走了很久很久的路,见了很多人和事,但一醒来就忘了。
如娘见她醒了,便替她整理钗环发髻,“姑娘,眼下我们很快就要到新渡口了,要改走水路了,我们搭船去永安,你不久就能见到你爹了。”
“我爹?什么爹啊?娘,娘呢,她去哪了?” 令徽急切地问,“傻姑娘,你糊涂了啊,夫人已经不在了。” 如娘攥着手帕,眉目间一片哀色。
令徽怔住,她的眼前忽地闪过重重叠叠的人影,头痛欲裂。
“啊……” 她忍不住喊出声来,如娘见状,忙把她揽在怀里,给她按着头,“姑娘,姑娘,快别想了。”
令徽的头痛得到缓解,她依偎在如娘怀里,默不作声。
她的眼里满是伤心和迷茫,自己仿若置身于一场梦里,梦醒了,娘亲却不在了,多了个素未谋面的爹。
如娘看着她,叹息一声,她如何不知令徽的所思所想,看着怀里年岁虽小却已出落得明艳动人的令徽,想着她以后的日子,顿觉心中酸涩不已。
折下那枝梅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花甜楚之意难平
- 简介:真假女主天下皆知的感情阿兄是个哭包相信女主是个仙女的小药罐女主想要的可不是这个,远离男人活的长久他看你的眼神可算不上清白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他可以毁了一起,包括自己大女主爽文
- 2.9万字2年前
- 愿君卿安
- 简介:【本文已签约⊙禁止转载】虐文警告非纯虐文,只是不完美结局。【江南晚】×【江执】那天下了好大的雪,我的神明江南晚将我带走,给了我家。“你……可愿同我回家”那天依旧下了好大的雪,我的神明跌落了,她走了,带着我破碎的心。“阿执,我想回家了……”“我的阿晚,你的信徒来寻你了……”
- 4.5万字1年前
- 团宠帝后马甲多
- 简介:作为一个虽是废物却集宠爱于一身的相府嫡女,却拥有上一世在21世纪的记忆,所谓废物,明明是被下毒,且看她如何扭转乾坤,一双凤眸睨天下,尔等奈我何?只是与她有着纠葛的国师,好像没那么简单,她的身世也……(1v1,双洁,狗血文,非穿越,世界纯幻想,勿杠,副cp超多,也会有狗血梗,介意勿看)
- 1.3万字1年前
- 神医狂妃:九王爷宠妃宠上天
- 简介:东方灵梦是21世纪的金牌特工里以唯一一个用医高手,因为被姐姐一刀刺死。穿越到了灵华大陆,灵华大陆是个武为尊的大陆,的护国大将军的二小姐,是个草包废材,从小便被测试出没有灵根,不能修炼武功。被后母陷害下毒而死……东方灵梦穿越到了护国大将军二小姐身上……东方灵梦一拳打白莲花大小姐,一脚踢后母沐氏。世人说她没有灵力笑话。炼丹宗师很稀有,她分分钟练丹,送给灵兽吃“糖”,世上神器几乎没有,她分分钟练神器,一练几十把。一人最多只能驯服一只灵兽,她却驯服了一群灵兽。可谁告诉她,为啥妖孽的九王爷,一直缠着她……“梦儿,我来暖床了。”某人死皮赖脸的不走,她“滚。”某人“我还没暖床呢,不能走。”她一头黑线。“你不走,我走。”他“你要去哪?我跟你一起走”东方灵梦一头黑线,到底为什么这个妖孽会常常缠着她呢?不就是救他一命吗?………(各位读者,看了写个评论或赏个金币,谢谢,各位亲)
- 2.4万字1年前
- 无盐王妃
- 1.4万字1年前
- 久违了,康宇辰
- 0.4万字10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