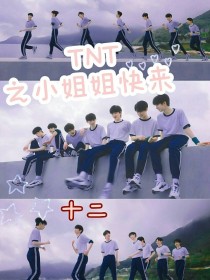第三十八章:药
杨九郎捏着勺子的手微微一颤,勺里的白粥差一点儿就撒在了张云雷身上。伸在半空中的手顿了好一会儿,他干脆收了勺子重新放进碗里,有一下没一下地搅着碗里的白粥。一双微薄的红唇有些苍白,嘴唇微微翕动却不闻一声。
好半天过去,碗里的白粥从烫嘴变得温热,他咬了咬紧抿的唇,抬头对上张云雷递过来的目光轻轻摇了摇头:“别说了,小辫儿。”他吸了吸鼻子,敛去眸中那些复杂的神色,舀了白粥再一次递到张云雷嘴边,“来,先把粥喝了,其他的事一会儿再说。”
“嗯……”张云雷下意识的答应了一声,就着杨九郎的动作一口一口喝着白粥。
小菜白粥本就清淡,他吃得更没有什么味道了。他受着伤,又淋了雨发了烧,要不是杨九郎执意喂他,他根本没胃口吃菜喝粥。一碗白粥见底,杨九郎一面收拾菜碗,一面撤下了放在床上的矮几。菜碗被放到了一边,他不着急把菜碗拿出去,坐在床沿上同张云雷嘘寒问暖了好一阵,喂了水、擦了嘴,施施然一副乐意被使唤的模样。
“翔子,别忙了。”张云雷拉住手脚不闲的杨九郎,硬扯着他坐了下来,沉下声音,认真地和他说道,“翔子,你不用照顾我了,我能照顾好自己。”他像是个做了坏事的小孩,偷偷抬眸去瞧杨九郎,“伯父既然吃了药,最近你多去陪陪伯父吧,我这里没事的,不就是一点儿小伤吗?我好好养着,没几天就好了。等我烧退了,咱选个好天气,一块儿陪着伯父、伯母出去走走。”
“哎。”杨九郎满口答应,手上却很小心地伺候着张云雷躺下了,“您先躺着,过两天退了烧,伤口也该结痂了。我再陪你一会儿,爸那儿有妈陪着,我过一会儿再去。”
张云雷其实是个挺怕吃药的人,从小就不肯乖乖喝药的。小时候生了病,郭先生端着药好说歹说,说了好半天,连一口都没有喂进去。郭先生着了急,拉着一张脸凶巴巴吓唬他,这才教他乖乖喝完了一碗药。
长大了,他还是不爱喝药,偏生身子骨又比常人弱上几分,每年都要生上那么几回病。还没有和杨九郎搭档的时候,总是梗着脖子说不是什么大病,过几天就会好的。他这体质哪里是过几天就能好的?几天没吃药,几天之后就躺床上了。师兄弟几个朝郭先生告了状,得郭先生亲自来一趟才逼着他喝了药。
再后来就是和杨九郎搭档,杨九郎本就是个心细的人,对他便更加心细如发了。不过,有时候他伪装得极好,病了也不教人发现。等到杨九郎察觉出来的时候已经病得挺厉害了,什么演出、什么背词,杨九郎拖着他去休息。他闹不愉快,不肯喝药,杨九郎就亲自一勺一勺的喂,汤药见了底,杨九郎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掏出一颗蜜饯塞到他嘴里。
杨九郎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反倒教他有些哭笑不得,次数多了,他喝起药来也乖了不少,反正每次都会有甜甜的蜜饯等着他。
如今……蜜饯是没有了,家里原本就没有备着蜜饯,再加上这次回来得极,张云雷又习惯了强撑,实在熬不住倒下了,哪里有空去街上买蜜饯啊?杨九郎已经很辛苦了,何必再拿蜜饯的事烦他?以往啊,他是存了几分逗弄的心思。现下,他连休息都乖乖听话,更不用说喝药了。
也不知道是该夸那药的药效好呢,还是该说杨九郎的父亲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了。小小的一个瓷瓶一共就只有五粒药。张云雷退烧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医生也来过几次,说他手臂上的伤开始愈合了,只要没什么大动作是不会再有事了。可,这一边是好了,另一边却愈发严重了……才三天,五颗药就只剩下一颗了。
这几天杨九郎和伯母都没有好好休息过,几乎是日日夜夜的守着伯父,就怕出什么问题。两个人的眼睛都熬红了,眼里布满了血丝,干涩得连泪水流流不出来了。
一大早,天还没亮,阖眸不到四个小时的杨九郎就爬起来去替了在伯父床边守夜的母亲。伯父本意是让他们都去歇着的,用他的话说,吃了药身体都好起来了,跟正常人一样,浑身上下都轻松得很,哪里会有什么事?
他是这么说,但所有的人都知道,那药是在调动他身上最后一点精气神,耗空了,人就没了。杨九郎因为师门和三庆,一年都没回家几回,现在又遇上这档子事,他哪里还睡得着,怎么说也要守在父亲身边。哪怕就几天了……
张云雷:戏子多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TNT:夜光变奏曲
- 简介:在光与影中摆动身体,跳出华丽的舞步,夜色梦幻让我们握住你的手指共同奏响暗夜曲调。美!在我看来实在是太完美了!站在这里所有人都在发出感叹,目光痴迷的盯着少女。能够被上帝称赞的完美造物,每一刀的落下都是经过周密的计算,关押在培养皿中接受别人恶意的目光。一家市中心医院内,心理医生收回了办公桌上的治疗单子。【患者:余筝】【病情:被需要人格】【需要治疗原因:全身心性交付给他人,剥夺自主性人格。】【治疗建议:放弃。】(TNT全员,科幻异能产物)(内容纯属娱乐,请勿上升真人。)
- 4.9万字2年前
- 王牌对王牌7:吃糖进行时
- 简介:—【日更】已签约宋亚轩&沈琦糖萨摩耶&小白兔—暗恋很久的女孩子和自己一起拍综艺,怎么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呢,那当然是要一步一步拐回家啦~—灵感很慢剧情也很慢—〈话本世繁华,奶思尽风流.〉—22.02.26初发图片来源堆糖/微博侵删—
- 45.8万字11个月前
- TNT之小姐姐快来
- 简介:阮江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在家看电视看的好好的,突然被一个叫小可爱的系统绑定,还要让她去攻略七个大美男。什么?美男?!阮江大声吼道,还有这种好事,老娘去定了!不过,这怎么和想象的不一样,一个比一个粘人,说好了啊,老娘可不动真心…………〖第一位面:领家温柔哥哥马嘉琪✨〗〖第二位面:傲娇豪门少爷丁程鑫✨〗〖第三位面:可爱阳光学长宋亚轩✨〗〖第四位面:霸道酷拽男孩刘耀文✨〗〖第五位面:清纯干净学霸张真源✨〗〖第六位面:高冷害羞学弟严浩翔✨〗〖第七位面:幽默沙雕网红贺峻霖✨〗PS:这些都是现代位面哟,如果有人喜欢,作者会考虑写古代位面的!
- 2.2万字1年前
- 田嘉瑞:我想我们在一起
- 简介:甜撩跳脱小戏精✖️阳光纯情小醋包故事情节纯属虚构,人物性格全部自设。不定时掉落甜甜小剧场。首都电影学院毕业的贺知荔日常爱好是窝在宿舍追剧,毕业愿望是能和田嘉瑞出演同一部剧。贺知荔:“宫三先生是我的!是我的!”一句‘姐姐’听了几十遍。云之羽,一追一个不做声。偶然的一次饭局上,已经毕业的学姐引荐她去参演一部小网剧的女主,没想到火了。“下一部戏,小荔有没有想合作的男演员呢?”一次采访的提问中,主持人如是问。贺知荔认真的回答。“田嘉瑞。”还没等到下一部剧台本,就收到了《我们的客栈》综艺常驻嘉宾的邀请。助理姐姐:听说田嘉瑞也被邀请了呢。贺知荔:“好好好,第一次综艺是你,第一次恋爱也得是你!”
- 1.5万字11个月前
- TF四代:捣蛋鬼不许捣蛋了
- 简介:(兽世)懵逼了,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咋滴,我哥还来了?哥,你见过谁把妹妹往外推的呀?放开我不跟你们走,不跟你们结婚,不跟你们生崽崽!好家伙,你们一个个深藏不露是吧,那好跟姐斗,走着瞧,我一定让你们这里鸡犬不宁,扰的你们坐立难安,哈哈哈哈,我看谁还敢娶我?
- 2.6万字10个月前
- 叩拜
- 简介:【短篇be】<br/>“我向佛祖三叩九拜,愿殿下无疾无痛,平安喜乐...”<br/>——————<br/>“今朝若是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
- 1.4万字10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