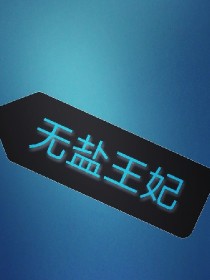六、绝处逢生
褐衣人大约有四十多人,是镖队的两倍。看他们的兵器和武功路数,显然是出自同一门派,却看不出源于谁家。短刀虽然不符合兵器“一寸长,一寸强”的说法,但却更称手,易于掌握,用得熟练者,杀伤力丝毫不弱。镖队这边,除了谢青华使枪,其他人都是用刀,优势是圈子大些,短刀不易近身。
那些褐衣人似乎知道谁的武功更厉害,很快就各有五个人将陈易安和居仁福围住了。谢青华的一杆长枪倒是发挥了优势。他连声长啸,将枪舞得气势如虹,瞬间将包围圈荡开数丈,打开了前方的道路,趟子手们便急忙催车前行。
陈易安深得万壑风的真传,刀光如雪片也似,撒下一片杀气,褐衣人稍有不慎,躲得慢些,便见血见肉,不得不缩在刀圈之外。陈易安见这些人并不十分难以对付,紧张情绪稍稍缓解,心里却担心起游晚虬,这秀才遇到兵,他可怎么办啊?陈易安一边护着镖车,一边四下寻找游晚虬。忽见一小撮褐衣人起了一阵骚乱,一道碧光随着游晚虬的身形腾跃而出,碧光所指处,褐衣人应声而退。
他竟然会武功!陈易安又惊又喜。先还以为这小子会成为累赘,现在好了,倒多了个帮手!陈易安看着游晚虬身形舒展,如惊鸿游龙,手中一支玉箫挥洒而出,碧雨点点,转眼间帮他打退了左边的两个褐衣人,不禁心中叹服:还是师父眼光毒啊!
然而刚前进几十步,褐衣人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包围圈,从四面八方攻上来。趟子手们顾上不赶车,纷纷拔刀迎战。陈易安沉着指挥道:“仁福,前面开路,护送青华出去。我断后。”
说着换到车队防御薄弱的另一侧,左挥右挡,将一群褐衣人逼出圈外。立刻,游晚虬又将这些人接住,挡在了镖队的后面。两个人互相配合,趟子手们压力顿减,可以集中力量催车前行。
“晚虬!快给家里报信!”陈易安一刀架开敌手,随手把那包银子扔了过去。这是万当家的安排,他必须执行。
游晚虬接过银子,匆匆道:“知道了。”边说边身形一晃,来到一辆镖车的后门,开门取出一只鸽笼。镖队每次出发,都会带上信鸽,以防不测。
“没有笔纸!”陈易安见他还有功夫去取信鸽,不禁急了。
“我去找!”游晚虬刚将鸽子笼取出来,便又被包围,他一个腾身,如鹞子般斜掠而过,几个褐衣人纷纷中招,鼻青脸肿地退开半圈。然而游晚虬迅捷的身形也随即慢了下来,因为鸽子正疯了似的乱扑腾,他真怕动作太猛把鸽子掼死。
陈易安见他心细如发,忙而不乱,大感欣慰。计算着突围问题不大了,便担心起师父来。边护镖边偷眼回望师父,然而趟子手们在危急之中发足狂奔,已经跑出半里路。人多草高,已经看不见师父了。刚一分神,只听身旁有人惨叫,连忙回转来一看,已有趟子手受伤。他心头怒火中烧,手中刀越发使得凌厉起来,转眼砍倒两个褐衣人。对游晚虬道:“也好。放完鸽子赶快回来帮忙!”
居仁福一手牵着一匹马,另一手挥刀,从队伍中段奋力杀到队伍头部,口中喝道:“都给老子让开!”眼见杀开一条路,终于来到谢青华身边,高声道:“青华,这匹马快,你快去搬救兵!”
谢青华也不客气,飞身上马,道声:“各位保重,我先去了!”借着马势,一条枪舞得如蛟龙出水,势不可挡,将挡在前面的褐衣人扫出七八丈外。
通道一开,趟子手们不管不顾,拼了命拉马推车向前奔,整个镖队一下子窜出了包围圈。居仁福在前开路,陈易安断后,混乱的场面开始变得分工明确,有条不紊。
陈易安便催道:“晚虬,你报信要紧。快去!”
游晚虬一手握箫,一手拎着信鸽和银两包袱,着实有些不方便。口中兀自问道:“哪里有笔纸?”
“不知道。”荒郊野外,笔纸还真不是寻常之物。陈易安只管催道:“你快走,反正你的箫也不能当刀使,万一再出岔子,不要连个报信的也没有!”原来,陈易安已经看出,游晚虬虽有深厚的武功底子,但箫毕竟是玉制之物,与兵器硬碰,极易粉身碎骨。是以游晚虬只能避其锋芒,以点穴、借力、拳脚之类的手法应对,战斗力大打折扣。
“好,我报完信再回来帮你。”游晚虬刹住且战且退的脚步,迎着褐衣人冲杀过去。一时间,他被团团围住,为镖队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与劫匪拉开距离。只是游晚虬也不可能拖住他们太久,更何况,在褐衣人之中,有两三个武功实属一流,刚一交手,游晚虬便知不是可以随便应付的。手中没有合适的兵器,又要保住鸽子活命,不敢恋战,只得抽身向外冲。而这些褐衣人的目标是镖货,见一时拿不下游晚虬,索性让开一条道放他过去。
再说万壑风,在这场护镖之战中,他的压力是最大的。尽管他的滚雪刀法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刀一出手,便舞得如片片飞雪,但面对双钩,他的招法显然不那么适应。钩法的变化极多,且是专门对付刀剑一类直兵器的。从交手那一刻开始,万壑风始终觉得前心后背、上下左右,到处都受到了威胁,一口宝刀左架右挡,忙得如翻江倒海,依然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而何不必的双钩却始终不离万壑风的要害三寸。不出十数招,便将万壑风的胸前衣服划破好几处。幸运的是,万壑风并未受伤。何不必心中犯起嘀咕,双钩压得更紧了。谁也不曾有一丝一毫的分神,每一招出手,都贯注着十成的内力,如排山倒海,汹涌喷发,一丈之内,有如一堆无形的铜戈铁矢在互相厮杀。
忽听“嗤——”地一声,万壑风的身形蓦然一缩,退出圈外,左臂的衣服已然被划出一道大破口,不过只渗出少许鲜血。
“铁臂功。”何不必忍不住赞了句:“名不虚传。”
铁臂功是万家独门绝技,能在瞬间将内力贯注两臂,使手臂如铜浇铁铸一般,产生巨大威力。如果不是有此功护身,这只左臂已经断了。万壑风知道自己无法取胜,唯一的生机就是尽快撤逃。他没有时间观察镖队的情况,但能听到大伙越去越远,想来突围无忧了,便故意拼着让左臂受点伤,硬抢出撤逃的时机。
何不必的双钩立即追了过来,看来他是铁了心要万壑风的命了。
万壑风不能去追镖队,只得急急向河边奔去。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拼命了,虽然每天也练刀练拳,但这些年四平八稳的富足生活,让他在阵前的反应能力减退了不少,一番厮杀,累得他心慌气短。还没跑出半里地,何不必从后追上,“刷刷”两钩,结结实实切中他的后背。然而奇迹又发生了,万壑风背上的衣服被划破,却居然毫发无伤,反而借着钩力,逃得更快了。
这回,何不必彻底明白过来,“哼”了一声,自语道:“这老东西穿了什么宝甲。”说着,继续穷追不舍,挥钩直取万壑风的头颈和下三路。
万壑风且战且退。幸亏有家传宝物麒麟甲的庇护,否则今天已经死了好几次了。可是麒麟甲只能护住胸腹,其他部位就得靠自己了,头颈自然是要全力护住,下三路就比较难以周全,加上年事略高,双腿终究不似年轻时那么灵便,不多时,已经伤了几处。
好歹总算到了河边。万壑风知道,在岸上打,自己必死无疑,只有跳入河中,才有机会改变眼前的死局,或有一线生机。然而就在他转身全力一跃之际,何不必一钩上来,准确地钩住了他的膝盖窝!万壑风右腿被挂住,左腿几乎悬空,根本无法稳住身形。而另一钩又朝他颈项扫来,他竭力挥刀一挡,自知若再不脱身,死亡就在下一招等着他。是以不计后果,腾起左脚猛蹬钩住右膝的弯钩,硬是将右腿从钩弯中挣扎出来。按他最坏的打算,准备拼了这条腿不要。好在总算是脱出来了,代价则是右膝以下的皮肉几乎被刮了个干净,白骨外露,鲜血喷涌。
随着“扑通”一声,万壑风直直地坠入河中,河水立即被染红一片。何不必盯着河水,在岸上不紧不慢地跟着。半晌,万壑风才冒出来换了一口气。看他的样子,真是疲惫至极,不知道下一口气还能不能上来换了。
正在这时,下游划上来一条小船。一个高个青年戴着斗笠,悠然站在船头。看不清他的上半边脸,只能看到下巴的线条清晰俊朗,精致的嘴角微微上翘,透着几分洒脱,几分风流。他很快注意到眼前的情形,侧目看了看岸上的何不必,又看了看河水,忽然一矮身,伸手向水中一抓,“哗啦啦”一声,将万壑风从河中提到了船上。万壑风块头不小,又浑身湿透,份量实在不轻,然而这青年却一抓而起,足见气力惊人。只是船头猛地一沉,把艄公吓了一跳。
斗笠青年低头检查万壑风的伤势,见他双目紧闭,气若游丝。还未及再细看,岸上何不必单钩一指,喝道:“把他给我!”
青年抬头瞟了他一眼,吩咐艄公道:“调头,回去。”
艄公刚要调头,何不必那头火了,威胁道:“船家,你若不把船撑过来,我就杀了你!”
艄公见他的兵器怪头怪脑,还滴着鲜血,着实害怕,偷眼看那斗笠青年。青年冷冷地道:“你若敢把船撑过去,我现在就杀了你。”
艄公犹豫片刻,指着斗笠青年,朝对岸何不必陪笑道:“这位客官已给过钱。”说罢,也不再管何不必,顾自将船调头。
何不必见状,二话不说,挥钩削向河边的灌木,大大小小的树枝树杈纷纷飞向河心,很快铺出一条路来。他一展轻功,飞身上了这条路,直扑小船。艄公一见,慌忙跑到船头,与迎面而来的船客掉了个个儿。
斗笠青年也不含糊,立即拔刀相向。“叮当”两声,便过了一个回合。何不必发现自己轻敌了,此人刀法之高,竟然还在万壑风之上。若在陆地上,他当然胜券在握,但现在,因为没能在一招之内抢攻上船,他又被逼回了水上,而水上这落脚点实在不美,难以变换步法角度。
又过了一招,何不必还是没占得便宜。那青年的刀似乎特别厚重,相比之下,何不必的双钩钩头偏薄,有些不敢硬碰,而且这刀,竟似有些熟悉!
两招即过,他们已经没法交手了,因为小船正如离弦的箭一般,飞快地向下游划去。而何不必脚下的树枝树杈,却因没有动力,只能顺着河水慢慢漂动,被远远地甩下了。
“站住!”何不必气急败坏,徒劳地嚷道:“萧山老妖是你什么人?!”
斗笠青年哈哈大笑,也不答话,扬长而去。
梦回陌上人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穿越:美男撩不停
- 简介:这人很懒,啥都没写。
- 3.5万字1年前
- 替夫从军
- 简介:楚令曦是灵国大将军楚志辉之女,疾恶如仇,天不怕地不怕,做事果断,也是因为遇事不平总会出手的个性,结识了很多好友知己,但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沐槿辰,皇帝之子,胆小,但又活泼爱闯祸,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原本都应该对小儿子是最宠爱的,可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个舞姬因此很多人都会欺负他排挤他,只有他的皇祖母最疼他。虽然吊儿郎当,但他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为了生存不得不隐藏起来。因灵国与潼国交战,灵国皇帝深知楚大将军实力强大不好控制,于是给楚大将军的女儿楚令曦与自己的儿子沐槿辰赐婚,是为了让楚大将军放心,也是也是为了牵绊沐槿辰。然而两人成婚后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沐槿辰是否能如愿以偿呢?
- 5.5万字2年前
- 花败枝残情未止
- 简介:【已完结】他靠在梅花树上,身上落满了花瓣,手中仍攥着那截枯枝,众人将他葬在了梅花园,随他入土的,还有那截怎么都取不出来的枯枝……
- 12.4万字2年前
- 腹黑王爷的武林高手
- 简介:完颜雪在酒桌上错拿了完颜萍妹妹的酒杯,回府邸时已经天黑。完颜雪觉得自己的头万分重又下着大雨在山上避雨,一路上也没什么地方可以休息,最后来到一个悬崖下有一个洞,他就顺着洞进去,谁知这一切却是万劫不复,洞里居然还有一个受伤昏迷不醒的王爷,完颜雪“这里怎么还躺着一个人好像受伤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先解了身上的迷药再说”就这样俗话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三年后温岭君再次来到江南是完颜思源“娘亲,快来呀”,完颜雪“小宝,你慢点”突然间完颜思源突然停了下来,看到身边路过的男人。完颜思源“娘亲”完颜雪“小宝,怎么了”完颜思源“那个人跟小宝长得好像。”完颜雪立马带着儿子跑了
- 1.8万字1年前
- 我要闯江湖!!!
- 简介:未改编完成,请勿入坑
- 2.4万字1年前
- 无盐王妃
- 1.4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