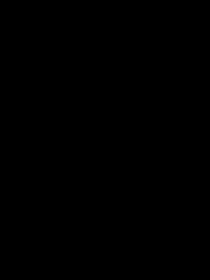第四十一章 道士下山(十一)
第二日,天罕见的下起了冰雹。
云摧城,花草折。拇指头大小的浅白冰点似算盘玉珠,乒呤乓啷,扫卷整座平阳城的长街小巷、酒家食店、矮屋高台……皆被这滔天冰弹射的砖瓦过痕,浅浅微融的冰点一半隐在暗,一半映照着轻盈的半盏天光……
屋檐上的瓦片也被天外来物炸翻了腰,黑色的残瓦在半空欲落又止,接着又是一阵落盘声响起,那欲坠的残瓦饱受欺压之后,斜斜的从黄土制作的墙面极速摔下,啪嗒——
瓦片应声四裂,残瓦犹如升空过后的绚烂烟花,随着源源不断从天穹倾下的万千冰雹并展过后,再无踪迹。
失去方寸之瓦的房屋,由那正方口处倾斜下一道亮白的光。一道接着一道冰点颇有节奏的从那破绽处千条万绽,点落成线,圆滚滚闯进屋舍里来。里里外外的地面上瞬间铺起了层浅浅的冰点,就跟下到锅里浮出头的小白汤圆一般。
楚鹤梨无语抱头,抬头,皱眉朝着屋顶上接二连三冒出的小洞怒视去,星星点点、无数冰雹砸地她透心凉、心飞扬!
虽说,江湖儿女不拘小节,但好歹不能连住的地方都穿窿哐顶!你看,这洞越来越大!简直都要比夜里的满天星辰还要敞亮……
“小云子,你快去把屋顶修修吧!这屋里叮叮咚咚的,都快赶上危房拆迁了……”不告而入的冰雹咚咚响在了楚鹤梨结实的脑瓜壳上,苦不堪言。这冰冻的她头皮发麻,这屋里也没几个能藏头的地来。
小屋也不知有多少年头了,蛛丝密布,连吸口气都是岁月的沉淀。
里面的木床桌椅不是被白蚁啃噬的千疮百孔,就是腐烂的都应该快要长出红通通的毒蘑菇来。积尘都有五尺厚,踩一脚,陷一脚。但好歹过来的时候这屋顶还算坚强,连丝缝隙也没给外面的蚂蚁留窗开户。可就过了一夜就脆的跟豆腐渣一般,估计等这阵冰雹过后,不用出去也能晒到早晨初起的太阳。
她急不可耐地用脚踹了踹身旁磕目打坐调息的谷云子,催促他快想想办法熬过这一难吧!
谷云子方才悠悠转醒,其实这动静他老早就把他给吵醒了。不作为,就只是他不想动。
他微微挑眉,任由天上恍惚下坠的冰雹砸在他头,或脸,或臂膀,或手背……一副恍然无物的姿态。这冰凉是凉了点,跟后槽牙咬了雪块一样酥酥麻麻的,倒也还能忍受。
他看想不远处抱着脑袋的小姑娘,有点失望。
这冰雹不像免费按摩吗?怎么一副避之不得的模样?
昨天他和她被街上的人包围说教后,楚鹤梨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他一路详聊。
天南地北、吃喝玩乐、人土风情。连她几岁换牙,几岁能跑能跳都说了,就连她逃婚的事情也从头到尾讲了七遍。
楚鹤梨是说的口干舌燥,而他只是适当的点头应和,用的还是万能句子。
“你说的真不错。”
“有道理有道理。”
“嗯嗯嗯……”
结果最后他连敷衍她,都懒得敷衍了,闷头赶路,一言不发。
楚鹤梨只能抓起头皮对天长啸!她很希望老天爷能下点刀子来!好捅死这个不懂风情的臭道士!
她疲惫地垂下了紧捏着他肩角的小手,晚霞正在起伏的山岚里翻腾,给他们俩重叠着的背影,染上了时光的浓度。
谷云子的发丝在这瑰红色的霞光里泛起了金色的光泽。
真好看,她看得一愣一愣。
可惜他,不懂她。
我说了这么多,他怎么连点表示都没有?楚鹤梨翻来覆去的想着,背着她的人终于说了。除你说的真不错,有道理有道理,嗯嗯嗯之外的第一句话来。
“再乱动,我就把你随便找地丢了。”说着还颠了颠她的身子,吓得她,刷的就把背的腰板挺直,端端正正的。
“喂,我都讲了这么多事情给你听了,你就不能也讲讲你的故事吗?”
她对他挺好奇的。
“我的故事?”他思索一番,接着问题回答道:“没故事,就一道士,无父无母的,从小在观里大,观里活。观里人多粮食不够吃了,就才下山来。”
楚鹤梨听着,原本她想象有关冷面大侠行走江湖的故事破碎了,她接着问他。“那你有姓名吗?”
谷云子点了点头,闷声道:“人都有名字,师父说,名字是依靠。”
“是什么?我先讲啊!”
“我叫楚鹤梨,楚就是那个楚,鹤是天上飞的鹤,梨是可以吃的梨!”
“嗯,挺好的。”谷云子琢磨了一下楚鹤梨的名字,发现除了通俗易懂就没什么内涵。
他弯眉浅笑,模仿楚鹤梨刚刚的语句敷衍道:“我叫谷云子,谷是地上种的谷,云是天上飘的云。”
此话一出口,他惊讶的发现原来他和她的名字倒也算半斤对八两,除了通俗易懂也没半点内涵。
楚鹤梨却开始反复默念他的名字。娇滴滴的声音,喊的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谷云子,谷云子?居然还有人姓谷啊,嘿嘿,我觉得还是叫你小云子吧!”
谷云子: “?”
来自无人区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龙宠—至高兽皇
- 简介:当帝国被残暴统治时,我们年轻一辈,怎能不管。Q群:927035474有事找助手:2544824254
- 8.5万字2年前
- 浩三故事
- 简介:《雨落银海,浩情三愿》番外
- 15.0万字2年前
- 在韩女爱豆
- 简介:JYP新女团PINKLADY
- 0.3万字2年前
- BE短篇—冉
- 简介:be短篇会写一些我曾经磕过的cp
- 0.5万字2年前
- 对妖玩偶(YL杂货铺)无偿封,字素字设,赠花
- 简介:现在是杂货铺,可以点击看完整简介。接单中,联系方式:Q群631350778“他”是一个被大家称为疯狂科学家的人类,只要成功了,他做出的玩偶实验品,可以被世人称为奇迹。“终于!终于,哈哈哈哈!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意识。这个实验,它将成为拯救人类的福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每天晚上23:30更新送花/封面/绘画/Q版字素/校园字设/男频字设,无偿/有偿接送花/封面/绘画,无偿,封面/字素/字设有偿接[需注意!!!有时候会出活动!]后期我会改成书籍,望收藏关注评论点赞,支持一下
- 10.3万字1年前
- 烦死老子了-d507
- 简介:穿越到入洞房,自己变成了个大粗汉,还是抠脚大汉的那种,不过新娘子真是漂亮!诶?诶?什么咋是个男的?啊!你不要过来啊!
- 0.1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