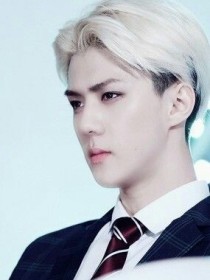【二】
比起我初来之时,长安城已然萧条了许多。
东市西市是最繁华的商贸之地,每逢佳节游人如织,我们所住的靖安坊偏南,人烟略荒凉,偶尔千相耐不住冷落,便在我脸上扣一张面具,遥遥拽着我去东西市乱逛。
如今将近过了十年,远方频频传来战况,听闻叛军集结邪门教派一并攻来,不知真假,东西市的商铺日渐衰败起来,胡姬酒肆之类更是一概寻不见,让千相大呼可惜。
我们终日浴血拼杀,也改变不了长安城四面楚歌的处境,妖物愈发猖狂,远方又有大军压境,如潮水渐近,无可奈何。
嗅惯了腥咸的血风,日复一日守在这长安城,黑暗中看不见一丝重归盛世的光,会让人感到十分的疲惫。那日李姑娘落跑后,便再也不曾溜出来找我,她没见过我如此残忍地剥夺一条命,或许这才终于想起来,我是怪物。
千相察觉到我日渐消沉,他叹了口气:“你受妖物蛊惑太深了,休息几日?”
“好。”
他说的没错,我的确在意那些妖物对我所说的话。
他们为什么都唤我云生?或许我在神智未开化之际,与他们有过纠葛?
我没有家人,也从未拜入师门,可他们呼唤我的语气,分明像是在呼唤同类。
我长久地躺着睡觉,昏昏沉沉,偏偏那大妖还在梦里纠缠不休。
大妖的身形居然渐渐清晰,我因眼盲,从未见过任何生灵的真正模样,不禁惊奇地看着他。幽黑的眼瞳,偏白的皮被宽大蓝裳遮起,头顶长发高束,他抬起脸,目光流露着和善。
“云生师兄。”
原来妖是这般模样,竟不似想象里狰狞。
“我没有名字,也不叫云生。”
“不,你只是忘了。”他轻声道,“那块玉佩,送还到陌师兄坟前可好?是他娘子刻的。”
我皱眉:“你们骗我,妖怪不可能有亲眷,也没有师门。”
“师兄,真真假假,你被迷惑心智太深了。”少年眼中悲伤,“只要你送还玉佩,我便不再纠缠你。”
我从梦中惊醒,想了很久,悄悄起身,未推醒千相,径自向坊外而去。
十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独自出门,从前千相怕我横冲直撞,总不离左右,久之也就厌了,放手不牵我,随我自己撞得鼻青脸肿去。他这人磊落,最不耻逃避,若知道我因疲惫而向大妖妥协,必定动怒。
我对时辰有极高的察觉,此时应是寅时,天欲蒙亮,晨钟声未起,但街角卖胡饼的王叔大抵早已起了。我摸摸袖里几个铜钱,叩响铺子木门,先填饱肚子也未尝不可。
“王叔,两张胡饼。”
无人应,难道王叔也搬走了?
我有些无奈,转而敲酒肆的门:“掌柜的?”
空荡荡的晨街,只有叩门声,长安城陷入熟睡般寂静,丝丝诡异感漫上心头,我顾不得吃饭,疾步出了靖安坊,一路竟鸦雀无声。天子在城北,百姓在城南,愈往南处愈发荒凉,尤其近年死者甚多,这些无人之地已被用作埋葬。
听说大多妖物的尸身已被烧作飞灰,草草掩在此地。
脚上布鞋被腥臭液体浸湿,这里尸气冲天,便是亡人埋骨处,我喘着粗气停下脚步,跪坐在地,用手刨开泥土,将玉佩放下去。
脚步声渐近,我茫然抬起头:“千相?”
“师兄。”对方停在我身前,清淡少年音,“你果然会来,随我们走吧,离开这里。”
我诧异警惕起身,四面八方皆传来脚步声,有轻有重,听得人心绪混乱。我正要出招,却被半空投下的一张铁网牢牢封住,铁爪钩入皮下,我痛呼一声,拼命撕扯身上铁网,却是越挣扎越紧。
“妖物!你们想做什么!”
千相说的没错,妖物不可信,我浑噩间一时大意,竟中了它们的小伎俩!
它们将我围起,一声声地唤着,有严厉,有亲和,有冷漠,有怒吼……
“云生!”
“云生……”
“云师兄……”
我被困在网中动弹不得,脑中嗡嗡作响,一线微光竟破开我眼中长久的黑暗,一幕幕从未发生过的光景掠过,原来我也曾见过这山河风光,也曾与他们并肩而战……
难道这一切都是蛊惑我的幻象?若不是,我以前究竟是何人?
“住手!”
千相的怒喝声暴起,我身上的铁网被一剑斩开,打斗声震天,血腥自他身上绽开,千相拽我往远疾行:“莫听,莫想!皆是幻象!”
皆是幻象……
刹那间,我回想起玉佩主人弥留前呢喃过的话,惊人的相似。昼繁华夜死寂的长安城,方才映入眼中的青山秀水……千相将我领回的长安城,与妖物所赐的光景,究竟哪方才是幻象?
相信谁?
千相与我长伴十余年,不会骗我!
我听了千相的话,紧紧捂住双耳,呼唤声戛然而止,微光随即熄灭。
果然妖物那一方才是蛊惑人心的幻象。
他自大妖的围困中将我救出,全身浴血。我们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走在归路上,我冷不防触到他手臂一道伤口:“好深的伤!”
千相幽幽叹一声:“我的实力竟降了这么多,以前可是自百敌中杀出都不是事儿。”
我从方才的事中扯回思绪,哑然失笑。
“你笑个什么?不信?改天定让你见识见识。”
“好好。”
“对了,靖安坊的百姓是不是已经搬走了?我听人说,敌军已经打到……”
“说什么胡话,这不是有人?”
我正要开口,忽然被洪亮的钟声打断,暮鼓晨钟,自钟楼敲响,一声接一声,余韵绵长,远扬长安城一百零八坊,千军万马催破长夜般的浩荡气势。酒肆、胡饼摊……长安城仿佛复苏,渐渐恢复生机,我错愕地抬起头,感觉自己再一次被这座城淹没。
天光拂衣。
让人疲累。
“我想离开长安了。”我轻声道,三分玩笑,七分认真。
“现在还不行,你还没见证乱世最乱的时候。”千相自言自语般补一句,“快了……”
我辨不清几分玩笑,几分认真。
他卧病在床这些日,我偶尔出门闲逛,眼看敌军将至,长安城又萧条了许多,连昔日最繁华的平康坊,也一派落败之声,逃不走的歌姬们没精打采地唱着曲儿。
李姑娘最后一次来主动寻我,是某日的黄昏,她向我道别。
“爹爹腿脚不便,逃不走了……他让我嫁人,随郎君一家出城去。”
诡长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叶.心有灵犀第一季
- 简介:只求一生一世,因为陪着你爱的那个人,只求永远一世,坚信着自己的信念,只求不念友谊,开始人生的道路——就是我的第一批作品。希望大家喜欢。我希望那你们看看什么是高富帅。有着怎样的气派。————(吴家二女安琪拉)
- 3.3万字1年前
- 元时代
- 简介:在大世纪时代出现了不同的职业重炮手,镭射眼,铁甲文森特……一代巅峰战神‘’零‘’从微末中崛起,带领‘’零杀队‘’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
- 0.2万字2年前
- 超级宠儿1
- 简介:25岁的苏幼檀在一次意外穿越在一5岁的孩子身上遇见了韩国名星exo并成为他们的妹妹
- 0.0万字2年前
- 天才少主
- 0.7万字2年前
- 妖仙物语
- 简介:她们是三界之妖彼此的仇人却化敌为友他们是妖的敌人仙却是彼此最喜欢的人……
- 0.3万字2年前
- 阴差办案小组
- 简介:一个由阴差组成的办案小组,专治地府的各种诡异案件
- 4.7万字1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