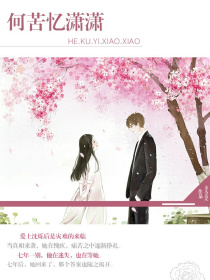弄戏(8)本章完
约莫有一盏茶的时候,她看见了齐秉文,以及他的那位夫人。她忙抬起头来,含着满眸的泪水,哑着声音朝齐秉文道:“齐郎,齐郎你救救我,你说过等你立了军功回来便接我入府的,你怎能食言呢?”
齐承喻心下早有了一番计较,眸光一转,朝齐秉文说:“秉文,这女人你可曾认识?”
齐秉文似是早有准备,朝前走了几步,躬身作揖,好不恭敬的朝齐承喻道:“回父亲,瞧着眼熟,却不知是谁,只记得应是哪个戏子吧。”
闻了这话,月痕蓦然抬头,惶惶的看着齐秉文,哭喊着说:“齐郎,齐郎是我啊,我是月痕,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啊!”
齐承喻闻了这话,将手一抬,周遭的下人便拿着棍棒上来了,齐承喻点头示意,那些下人便开始死命打的往月痕身上打。月痕哭着看向齐秉文,朝他哀求着。齐秉文皱了皱眉,背过身去不说话。
月痕的背上已被鲜血浸透,青石砖上的血迹已然干涸。终是昏了过去。
齐秉文背过身去极力克制着眼眶中的泪,嘴唇咬的似是能滴出来血。看着齐秉文夙夜念想的女人遭罪,夫人一时竟也不忍,遂起身朝齐承喻道:“父亲,既然秉文说他并不识得那姑娘,想来他与秉文也没有什么关系,您再这么打下去,可就真打死了。不若放了她,任她自生自灭吧。”
齐承喻素来疼爱儿媳,细思一番便叫停了。
那日后,夫人遣人将月痕送到了客栈,又请了大夫开了药,吩咐客栈老板不必为难她,便离开了。
屋子里头暗沉沉的,弥漫的是中药味儿。月痕瘦的如同芦柴棒似的手,颤颤着拿起镜前的盛着胭脂的小瓷盏。手指一抖,那小瓷盏便咕噜噜地滚在地上了。她撇了撇嘴角,喃喃道:“都说戏子无情,世人嘲弄,可戏子若有情,那便是自作多情。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情深不寿罢了。”
月痕从炉上温着的壶里倒了一盏药,从空中倾泻而下:“这一盏,祭那个曾经爱我的齐郎。”此时月痕的眼眶早已湿润。
“这一盏,祭那个曾经的月痕姑娘!”月痕此时的声音已然开始发颤,可她仍斟上了第三盏:“这一盏,祭这几年的那些好时光!”说罢,狠狠地将手里的药盏扔在地上。
月痕颤着步子走到窗前,伴着**十四年的第一场雪,环着无望从客栈的二楼坠落。那一瞬,石阶上似是开满了焚焚绽放的彼岸花。
齐秉文隔着门帘,含泪看着月痕伤心欲绝的模样,心中只觉若万虫啃噬,终是哀恸难抑,蹲在了墙角,以手覆面,呜咽着:“月痕,月痕,是我无能,是我负了你啊!月痕……”他只不停地唤着月痕的名字,最后竟失了声音。
是夜,满天的烟花腾空而起,不过须臾,便散落地只剩余烬。
烟花燃尽后,只剩硫磺味。
短篇小说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重生之最喜欢的你
- 简介:重生?重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是碌碌无为还是接二连三错过,不,重来一世自己的人生我要自己把握
- 1.8万字2年前
- 安晓明的凹凸路程
- 简介:简介正在更新
- 1.3万字2年前
- 我怎么会喜欢他
- 简介:何莹是个活泼可爱的女生,上学时期遇见了她的真爱,那就是男主李俊,李俊是个表面高冷,内心幼稚的学霸。他们在一次尴尬的场合中成为了死对头,日久生情,两人产生了好感,可又不敢表达。他们经过了重重困难,最终两人勇敢表白,幸福的在一起!
- 0.5万字2年前
- 眷恋温柔
- 简介:请认真看下去,么么叽
- 2.3万字1年前
- 何苦忆潇潇
- 简介:爱上沈烁后是灾难的来临,这场爱令所有人无法承受,她毁了宁小北,同时也给文欣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当真相来袭,她在愧疚,痛苦之中逐渐挣扎。七年一别,他在迷失,也在等她,七年后,她回来了,那个答案也随之揭开。
- 3.6万字1年前
- 00后的校园生活
- 简介:校园言情
- 0.3万字10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