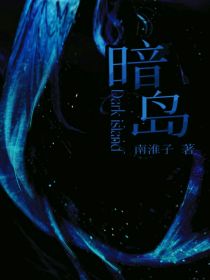民世篇 第八十九章 归元初现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一跃而下仅留三言两语,挂悬苍生天地,民不聊生,沦为生死炼狱病入膏肓,为孽为缘,无药可救。
传闻当初由此作为导致寻死的段久卿,临死前是非恩怨集一身,可她独独有话说给鹤容世听,道指此后她化为世间万物,皆是她。
菀菀类卿,说者有意,听者半分入心,他到底是忍痛生别离,纵使以往忍得了五年一生半载春秋,亦是含恨不下这一刻通入骨底,又是谁人意?
冷热不自知,白久自以为自己突如其来的得了这个孩子,会比传闻中的被骂得头破血流的段久卿会好混上一些,自得其乐也是好的。
可如今她这肚子愈发圆滚,这孩子时不时的动弹动弹,千方百计的让她怎么都不能疏忽不得,前些时候时常腹痛难忍,逼得非要鹤容世割血来的法力才能镇住。
白久归心似箭的往外逃出了殿外,蕊儿被她连拖带拽的,还不忘给她拍一拍背顺上了口气:“娘娘身子要紧,有什么吩咐?奴婢定为您照办。”
她这时分外警惕,白久也不多做脸色猜疑质否,抓着蕊儿的手五指扳了扳的拍案示意:“去寻一处就近无人的上等厢房,将这身华服换下来,我可穿不得它。”
“善容妃娘娘等等!”后头携腰间佩剑的叶红胥察言观色看出了端倪,快步进前拱手行了礼,“属下看您身体沉重,且在外时常有听说您身体一直因在外奔波,体弱多病,得需要赶快回宫修养的,着实来不及的话,属下可替旁人护送您回去。”
“是吗?好一个听说,本宫现下若真如你所说的神志不清的话,你难不成还知道以婵宫在哪?”白久不觉得这是嘘寒问暖,想得通自己连做什么有什么处境,外头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倒吸一口凉气遍体生寒,愤然出口成章:“我看叶将领无需多此一举,你我都是女子,难不成你也会不懂不同身难知苦处吗?”
“娘娘误会,您身体不适容易焦急,现下当务之急自当是该休息,而并非忍痛真跟着属下过去。”叶红胥也毫不示弱,满口客气却不见有低头口气的,“女子有孕是异常难得的,您怀的是中宫头胎,必然心思不定多生猜疑,可这是关乎您的生死,切莫随便拿来胡闹玩笑。”
“叶将领说的什么话,此情此景本宫都没笑,哪能跟你玩闹呢?”白久撒开蕊儿的手,双手侍礼站得挺直稳妥,转过头来双眸传神尖锐。
“……属下不敢,还望娘娘恕罪……”叶红胥对视一瞬突有如临大敌肃然起敬,一时不敢言语。
“这就怕了?”白久上下打量了叶红胥,一笑而过,“不管你怎么想,我忍痛也好真的无事也罢,本宫就是要去见一见民军众将士。”
话毕,她一手甩起广袖转身疾步而自行前去:“烦请叶将领稍后片刻,本宫更衣便回,之后劳您带路了。”
“娘娘说这话,是折煞属下了。”叶红胥的侠肝义胆顿时不敢大肆发作,拱手应了礼,不敢再抬头看白久,任由她朝着行宫远去。
“照老夫来看,这个重惊鸿体内是进入了什么东西,寄生在其中,才会让她焕然一新的重生了。”段印染身影渐渐折出,观现在中宫高台上,“嗯?原来这中宫里头自老夫离开一会,就已经这么热闹了啊?”
“您竟然没走?”鹤容世大为惊喜,正为这诈尸的事发愁,来了个人解忧自然是最好的,“无事不离三宝殿,您还有什么没唠叨的,突然记起,赶回来了?”
“净瞎说些孩子般的胡话。”段印染也不跟他计较做什么辩驳,侧身转头往后看去,“过来看看吧。”
“什么?”鹤容世不解其意,不以为然间讪笑道,“难不成太上皇陛下是想告诉我,看见这这片空旷地上站满了人,才会离不了半步抽身的?”
“你倒还聪明,如你所说,他们算是被你为难才会不打算回去的吧?”段印染这回倒是笑了,看鹤容世脸色淡了笑意,心头暗爽得很。
这颓废无所事事一事无成的赖皮狗栽了跟头,得了教训,倒也是好事。
“他们还在这做什么?”鹤容世吃了个大鳖如鲠在喉,厉声问着身后还在跪拜着的宦官,顿时大彻大悟的不止是天地动向,简直是流年不利,旗开得胜般的四方有堵了。
“回主神陛下,众大臣退出殿外之后,便一直在外候着,奴才怎么劝都不行,大人们也什么话都不说,恰巧方才来了要事通报,这才敢进来叨扰您……”宦官说话逐渐没了底气,声音越发细小,以至于最后不知什么时候闭口不言。
“滚下去!”鹤容世听他拖拉,如过了半年煎熬得很,心焦之余什么都没听出来痛骂了他一通狗血淋头。
“奴才告退,奴才告退……”宦官倒是麻溜得很,得了自在转头跑得极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臣等,恳请主神陛下,从众名门贵女之中择一人立为后,好安定中州,从此创下作为,以平民心!”古怪的是这边人一走,动静一呼百应,台下四万万遍布密密麻麻的人潮齐声骚动,“望主神陛下为我中州,即日择后!”
好一个摔杯为号的乘胜追击,鹤容世近日脾性烦躁,他虽容易意气用事,但却身为主神,此般更比白久还要让人随意左右操控。
这些个大臣都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精,况且依照鹤容世过去十几年的所作所为,能为一个忘恩负义不识抬举打他脸面伤他心的妖后沉沦这般久,毫无出息争气,自当无人看得起他。
许多事发生的多了自会被发现昭告天下,自地界翻新以后不少人都知道,他鹤容世自舞象之年便冠上了主神名讳,可谓一世无双,无人可及的神族传承直系之子。
得天独厚,不费力生来就可得的地位,纵使之后沦为报应旧地界,灭杀旧制度人类文明的使者之身,不被人所善待甚至是残害至死,他现下所得的一切哪会像是饱经风霜历经磨难后该有的珍惜自足的悔悟?
何止是众生不解,多少都是个把柄笑话人尽皆知,在这等针锋相对,煮豆燃豆煎前,逼不得已又故技重施,只因为早朝时候有白久这个晦气的卑贱后妃在,哪能算得上是商议大事,敲定局面?!
只不过是闹了个等同后宫争风吃醋的闲杂场面,鄙薄无聊,论长论短罢了。
“原来这就是中州的好大臣,一个个都以为自家养出来不读诗书,百无一用不沾阳春白雪的女儿就能当这中州皇后吗?”鹤容世呼出一口气,高声宣然道,“莫不是嫌命短,想跟我讨个送棺入土的赏赐,生怕中州皇后的凤冠霞帔,砸不住你们各家的泼猴是吗?!”
鹤容世再怎样都是读得圣贤书,知礼仪懂廉耻的,这种话说的这样大声,倘若不是中州皇城够辽阔,他这任意妄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性子得能耍到九霄云外去。
“陛下息怒,臣等并非此意。”这回只敢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他原本排站在最前头的,上前一步进言道:“事关我中州脸面威仪,善容妃白氏虽说是好,温良仁善,聪敏伶俐,但只是后六宫上下中馈账本而已,恕臣直言,这事连臣家中老妻都能做到,难不成还算得是个过人之处吗?”
“你倒也大胆得很,项上人头敢这么怒目圆睁的跟我说话了?”鹤容世嗤之一笑,“有道是父母德行代子出,来人,传我口谕,此臣从今开始全族降为庶人,尽数入我中州皇城宫中为奴!”
“是。”领命上来两个侍卫,一左一右的押下他,任由中间先前的出头鸟号啕大哭,奉命行事拖走往宫门赶去。
“果不其然患难见真情,这一出倒是有不少出头的佞臣,抓得一个又一个……不知太上皇陛下可有何见教啊?”鹤容世游刃有余,回头望着段印染问道,笑得双眸眉眼弯弯更甚了。
高台之下鸦雀无声,片片面面再无人说话顶对,唉声叹气面面相觑,都不知如何是好。
鹤容世这才称心如意,心知肚明段印染是明眼人,无欲无求,自然能说出来好主意的。
“主神陛下干什么难为老夫?我不过是个身外之人,想回去闲散喝茶,却被这些人挡住了去路,怎么,你还想让我给你指个皇后吗?”段印染可不想承这诺大的浑水,连忙摆手推辞,“好了,看样子我得走了,老夫告退。”
“哦?原来如此啊,我倒是突然想起善容妃她方才独自拉着叶将领,步伐极快跑出宫,她身子重得很,大早上的时候拉着她出来时,我虽徒手但都觉有千斤重,这会会不会出什么头重脚轻摔一跤的变数,可说不准啊。”鹤容世比他更是心大宽心放的开,似白久肚子里的冤种并非他的孩儿,无根无基的野种没了也就没了,耸了耸肩头有浮云游过,莫须有。
至于白久的生死他单手皆可平,哪会担忧她会不会因此一尸两命的道理,宫中里里外外都知道鹤容世这疯子癫狂,医官顶多是被以婵宫传唤去替他分身乏术时把脉的人手。
中宫的医术早已碰不得白久了,随她进宫至今,独获隆宠之最便得鹤容世日夜觐见,这早就烂嚼于人口,得千万妒忌了。
“那主神以为为什么善容妃会在朝堂之上于您背道而驰,竟会去帮着公孙大人说话?”段印染口快转了个圈,撕了鹤容世一巴掌,引得台下那些个大臣频频抬头,“她再怎的心性纯良也不可能平白无故多管闲事,毕竟谁人不知这姑娘一路颠沛流离,入了中州以后平平静静,闭门不出。”
“您的意思是是我邪性过恶,连最亲近之人都避之不及吗?”鹤容世索性快言快语,狰狞横脸的接了他的话,顺了他的意思,上前更近对峙。
“正如主神陛下英明所想,是又如何呢?”段印染迎火上尖,分毫不逊色上前,转而又伸出双臂同众目齐望对眼,酣畅淋漓道:“今日诸君可听好,主神不肯立后的确是为了白氏,可他铁了心不立任何人来当,是因他昨夜中宫强求所致!”
“太上皇陛下胡说些什么啊?前些时候听您刚关又放了东瀛的特使好一番闹腾,现下这莫须有的事都能来说什么算什么了?”鹤容世以地为脸,是真是假在他头上从来算不得是什么破天荒的霉头或是彩头,指摘了他昨日不久做的事,面笑而过,“的确是我问的不对了,您要是不愿,大可现在回去,我权当您什么都没说好了。”
他摆手甩了甩衣袖,先退一步不当回事,宽宏大量。
段久卿不在的十几年,鹤容世所在之处皆为炼狱,也不差段印染这回刁难,汗颜说不上,让一让就好过去了的,都不是什么大事。
他也算活的长久,所受过的事超乎寻常日以继夜接踵而来,即使是坐上了皇位,有了这宫阙万间,身上所留的疤痕依旧长在皮肉,只不过是时移世易了。
鹤容世十几年来行在外,想过以后再寻回段久卿,最好孑然一身,心无城府,归野山林,成双入影。
此间无人,无孤寂满清梦,天上人间求得此,归元活回儿时心,无拘无束,无牵无挂,了却牵扯,伴君左右。
“主神真当我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座上宾吗?”段印染心血来潮来了气,站在原地不依不饶,之前的事还拖到了现在,着实看得他心急,非要提他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敲定下来,势在必得咄咄逼人道,“我偏要在此继续说下去。”
“您还想做什么?”鹤容世见状不妙,定睛双眸紧缩,心骤停拔凉寒气返上,咋呼着踏出一步,脑中急迫交乱得却又想不出什么说辞办法来。
树欲停而风不止,不过是不懂其意,不合时宜罢了。
在场的谁人不是活了大半辈子,什么鸡犬升天好赖事人都过过眼的?眼下台下众大臣悉悉索索互语热腾鼎沸,骤然止声见段印染起手转袖,手中拿出人面大的面印来。
“这是!……皇族神印!微臣拜见太上皇陛下!”年长的一眼认出,率先屈身着急迎着金光跪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磅礴众声从远到近,重叠海浪翻潮而来,鹤容世亦在此时想到以往刚入云苏时,手里抱着书见着东宫有一处的高碑。
上头刻得密密麻麻流年经转磨损了字样,但最下头的碑坐便是这样的花纹样式,巍峨高百尺竟设在底端通地面,仅见过此等一面,而今回想起来,鹤容世一如从前跪下,不敢言语。
“中州皇城神印在上,我段印染当下以此作证,倘若有半句虚言假话,敢拿地界主神声誉为玩笑,必当不得好死!”他姿态起手高举在高台示下,决绝狠烈,毫不耽误快刀斩乱麻回头质问鹤容世,“善容妃是否真和主神陛下伉俪情深,那为何朝堂之上还敢放肆妄言,与您背道而驰,帮一个外人?”
着先在质问之下,鹤容世这时是真无力回天,双目皱眉一言不发,无话可说。
满眼净是段印染为何会如此大动干戈,动用如此威仪,低头以表认错默许,但他对此坦白从宽的道理都懂,竟不知自己和白久是差池在哪,何时出了嫌隙分歧的。
“现下大事当前,国中无后亦不能草草了事,你这主神不得人心,就连自己的枕边人也是如此看你,鹤容世,你可知道自己是多么一败涂地,一事无成吗?!”段印染再度连声质问一出,台下又起震撼骚动。
“看来这大言不惭的话,就连英明的太上皇也只敢拿着古物来说了。”听的别样较为清楚的,便是这一句话中刺两相,透心刻骨,又无可挑剔。
他鹤容世到底是昏聩而已,就算这位子上不是段久卿,更不是性情别样的白久,他迟早另择她人,再度重演而已。
白久的确中了公孙大人的招,但能旁观而看,她身为主神身边最近的女人,都能不信他,生怕他戾气过重伤及无辜,任性妄为到朝堂弥漫血腥,见不得半分井然有序,天理王法。
或许于白久而言,眼前人早已并非彼时人,所爱皆非,不复存在罢了。
仅仅是个罢了而已,又悄无声息的死了一条人命,生了一道怨恨,无可破解,难以道明其中千丝万缕,终究不动声色,嫌隙分歧入骨三分,眨眼睛间,便成了陌路人。
“一如太上皇训诫,我的确行事偏激狠厉,戾气过重难得人心,可白氏聪颖温良,贤良淑德,就算以假乱真代后出席,也对得起我中州,架得起威仪。”鹤容世索性坦然自若,抬手掀起衣襟,双膝前后相继跪地,“还望太上皇陛下恩准,倘若不能给她不可,这集国大会我中州罢免不去,又有何不可呢?”
“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口出狂言肆意妄为,便是仗着天地玄黄无人杀得了你,以正纲纪是吗?”段印染倒吸一口凉气,转而又大呼出一口收手没了天边金光,“方才在朝堂大殿之中,她可是亲手甩开了你的手,拉着叶将领抽身离去,这样大的脾气,你还期望她会再信你一次答应陪你同去吗?”
鹤容世执意白久也并非不无道理,她这姑娘周身有大东人的名门倜傥之气,现下十几年过去,无人再着古衣汉服,亦无人能着得起其气概风韵,但穿在她身上却浑然天成,脱似中州皇城失而复得的瑰宝贵女,再难有人可及。
便是如此以假乱真,再以身怀六甲为由让她不多说话,总比那些个从未戴过头冠嫌重的民间富贵人家的小姐,要好上不止千万。
不可置否白久现下仪态装束,的确是被鹤容世千金万宝浇灌出来的,但也不能辜负他如此用心,舍近求远就为了顾忌白久一片空白的出生,卑贱后妃而已吧?
“她再怎么说也是我的妻子,多少是会听我的,此事大可以交给我,晚辈在此叩谢过您英明神武,必当不负您所托众望。”鹤容世也是没脸没皮的,任由段印染撕破了脸面顺水推舟,他抓准了机会从水里爬上了船,自当不会不识抬举。
这说着鹤容世便拱手磕头行了谢礼,却看得台下众大臣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臣等不懂,太上皇陛下是定了什么旨意,竟未见诏书昭告?”还是站在最前头的那位大人,出步进言。
“哦?难不成尔等是瞎了?方才的金光还能看不懂这样大的召令?”鹤容世唏嘘不已,直身提着衣襟不曾抬眸正眼看去,出口却扇了他一个耳光,“立后本该是皇家家事,你这无名小卒一而再,再而三齐众在此,能见到听到,算是没把你当回事侥幸饶了你们多少条死罪,还不知足蹬鼻子上脸,以为中州皇城缺你们这点慵官占地费银子是吗?!”
鹤容世甩袖出手一道法力击退了这带头说话的,大发雷霆强打出头鸟,转身欲要打算回到大殿,又给了颗红枣打发这些个还在原地原封不动的大臣:“再在这碍眼,项上人头还要的话,这集国大会的琐碎事宜便交给你们,算是留你们这命有点用处。”
“僭越之罪臣等知错,必不负陛下所托。”带头的赶忙站起身,整理头冠衣帽的跪下,连带身后四万万不约而同争先恐后的齐声高呼而应,“善容妃白氏品行端正,聪颖温良,今日立其为后,是我中州大福,必与陛下伉俪同心,出席集国大会!”
“哼,一群惜命如私的蠢才。”鹤容世这才罢了一件大事,毫无顾忌的嘲讽道,“丢人现眼……”
“太上皇陛下可是要回去了?”又注意到了一边的段印染松着神经,依旧不打算离去,鹤容世又笑道:“方才这样大的阵仗定是费了您不少力气,需不需要我吩咐轿撵抬进来?”
“不劳烦了,老夫好手好脚,受不起主神这样大的抬举。”段印染嫌弃得不行,好不容易收拾好这烂摊子,归心似箭的只想回自己的小树林乘凉喝茶去,甩着袖子背在身后,“再说了您轿撵全是黑木,在外晒了一天,老夫嫌烫,坐不住。”
“太上皇陛下说笑了,那您走好,我还有奏折要批。”鹤容世日常跟他斗斗嘴,乐到了心里去,索性站在中宫门前目送他一身着白,行如飘渺,身姿绰曳消失于宫门折影而去。
常有异曲同工之妙,段印染姿态是和段久卿如出一辙的,常听说段印染真身是体态丰盈的雪狐,段久卿也相差无几,只不过是个女儿,免不了娇小玲珑些。
且段久卿经常习惯修炼功法,心经为武学,故此是丰盈不了,反倒是愈发纤细玲珑,姿容神韵清丽脱俗,由此而生。
中州皇城再像,也不似云苏皇城钟灵毓秀,接天得地,浑然天成红尘仙云相融间,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源头活水尽不在,枯藤老树独留昏鸦一只,此时再无彼时光,归元而去,终究奢求。
“世风日下,这太上皇果不其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三言两语就压制了主神,也不知白氏是他什么人,竟要这样帮着一个卑贱后妃!”只闻身后人潮袭来,叶红胥闻声回看,竟见无数大臣这才成群结队退朝走出,行在这去往宫门的必经之路。
“叶将领竟还在这做什么?”人多眼众,她一回头,自然是被发觉了。
“回这位大人,属下奉善容妃娘娘之命在此等候娘娘更衣。”叶红胥不得不答,拱手客气道,“诸位大人劳苦功高,我方才在此就察觉到了中宫动静,想必是处理定夺了一件大事吧?”
“大事确实是大事,但受不起叶将领如此夸赞,我等不过是奉命观景,和这事可毫无干系。”其中一个见了她,一下说出了心头苦水,“倒是心疼叶将领,这善容妃不见得是个善茬,为了拒绝这浩大殊荣,胆敢当着圣面拉着你做噱头离开,还得在这等她更衣,卑贱之人就是矫情!”
“娘娘总归是有贵命在身,但她脾气坚硬,不害于人,属下对她倒也敬佩,至于大人所说的矫情,我并不以为身怀六甲之人仔细些有什么不妥。”叶红胥到底还是锄强扶弱,因自己设身处地,不留情面的驳道,“后服头冠贵重,并非娘娘消受不起,拖累的是腹中孩儿,亦是中州储君,各位大人就算有火气,也不该任意对着女子孩儿置气,顶撞圣上惹主神不悦。”
“妇人之仁!”又在她这里受了气,忍无可忍脱口而出,“就算如此她也穿不得这凤冠朝服,本末倒置,有失规矩!”
“属下一介武官,不经常置身于宫中,自然对这些规矩不太熟悉。”叶红胥姑且以退为进,行了拱手礼,“大人无需再同我多费口舌,赶快出宫回去休息才好。”
“可有些人就是歇不得,心中琐事纠结不放,一闭上眼满追名逐利,叶将领何苦强人所难呢?”又问闻言两道其间,白久身影忽现走来,她无需搀扶,蕊儿只好跟在身侧低头随侍。
“方才是臣等失言,望娘娘海涵,安心养胎。”三两臣子见状行了躬身拱手礼,先走为敬,“臣等告退。”
“都下去吧。”白久蔑视着不同他们客气,甩袖打发,转脸对叶红胥道:“叶将领久等了,烦请替本宫领路吧。”
“属下领命。”叶红胥亦别无它话,拱手领命。
亦有归元之期盼,高崇甚远为信仰,心之所向,求之不得。
高山流水亦有所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分歧为路终同归,来年又见时,泪满襟皆叹遗憾,回想错从此生,不该相见,亦不应有情,天亦老。
——————————————
微末:
微末:端午安康
微末:六月快乐⊙▽⊙
明堂拾经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雪莲花的契约
- 简介:【本文原创,勿盗】【不喜勿喷】黑蝴蝶的继承人凌思娜,又是一个拥有雪莲花契约的人。雪莲花契约现世,凌思娜根据黑蝴蝶的指引,和闺蜜洛樱、黎雪,公寓主人白治华一起,开启了拯救父母的旅途。神秘出现的洞穴,毫无人烟的星澜国度,这些奇怪的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时间流过,万事皆空。——洛樱究竟有没有身世呢?随着探索的深入,这个秘密慢慢揭开。这是一个由魔法创造的生命,为的就是在末日时有所牺牲。但她自己,似乎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在这记忆之中,究竟潜藏着什么秘密?末日之时,洛樱会怎么样?末日之时很快到来,凌思娜和黎雪似乎有了拯救洛樱的方法。方法是什么?会成功吗?(逻辑上的众多问题不要在意,会修文)——你的命运,早已注定。——
- 8.2万字2年前
- 轮回后传之袭君
- 简介:轮回后传,这是继我的另一本小说,风灵手扎里面一篇小故事出的,应该算是后传吧!准备写一写他们的后世!一个是普通的天才少女,另一个是苍罗大陆的妖孽魔君,到底是纠缠还是桎梏,不说了?请看正文。
- 72.0万字1年前
- 妖后成长记
- 简介:她,是唐家弃子,天之骄女。她,是妙手医仙,索命毒尊。她,是千载废材,绝世鬼才。她,是渡人仙女,玉面修罗。……情,世间最毒的毒药。堕仙成魔,无怨无悔!不顾世人的目光,一切随心,快活逍遥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 3.6万字2年前
- 生生世世追寻你
- 简介:沙雕本雕凌依羽&腹黑本黑万俟御玄(mòqí)凌依羽,一名初三女学生。原本平静的生活,被一只橘猫打破。“喵呜,不许叫小爷笨猫!”.大学凌依羽一手捂着红透了的脸,一手指着面前俊美却衤果露着的男子“娘了个棒槌的!你你你……”……别看前期的男主是只傲娇做作(被打)的小橘猫呀~中后期会暴露出腹黑的本性哒~(并且是甜的甜的甜的!)
- 0.1万字1年前
- 《红尘散;狐妖世子缠上罗刹公主》
- 简介:这人很懒,啥都没写。
- 5.6万字1年前
- 暗岛:
- 简介:他是一个既世俗又浪漫的怪物,他曾告诉我做事想好得与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不过除他以外。你怎么看,我的爱人荒芜高峰,葱笼平原不过是原始海洋退下后的产物,这场战争只是为了生存和和平,死去的灵魂呼唤复苏,万千怨灵从海底来到海面……
- 1.0万字1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