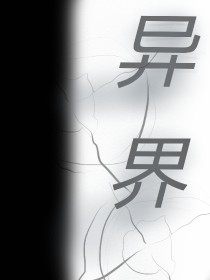民世篇 第八十一章 嫌隙
情愿所犯之罪为罪,不远从道之人性顽劣,冥顽不化固有因,报应轮回自有偿,自圆何其说?
此卷展开长河远,卷卷自有名,故以善其身,与众不同难相融,绝而生厌枉为生。
厌世顿悟不论长,年少有为处处生,生来到此坊间游,是苦是悲皆是大好,咎由自取,到头来才看的透想的清,活着原本才是那多此一举。
她这双眼睛再睁开时,天地颠倒,孑然一身,生前以往最重之人早随波流冲荡匿迹,忘了的想不起,记着的忘不却,强求不来,顺理成章。
正如当下,她所看见的天边流火,冒着日光猛烈边明亮橙红有颜色,刺得她眯起眼渐渐发花。
“流火而已,想必是外头的哪家仙门在玩弄法术庆祝喜事。”刃衣不以为然,瞥了一眼不当回事,“您还是别看了,久了伤眼睛,中州是为仙都,是有白日里放烟火的习俗的。”
“怪哉,难怪这里容不得别人进入,要是待上个三年五载,谁还会在外说中州是天上人间。”白久低头,余光悉见没几步就是以婵宫的白玉金镶的题字宫匾,照样惨不忍睹,不敢直视,“主神他人呢?”
忍受至今,这中州地方的风气以及条条框框,都不单单是简而易见的奢靡之风,反而更像是西方极乐,反人而为的怪事恒生,竟都是些这里的正常习俗。
要是没有当下她所住的这旧地,是她以前所住的广厦万间,鹤容世尚且不敢动一砖一瓦,算他有良心尚存了。
这中州看久了,待得时日长了,连红喜事都是瘆人发慌的喜丧,再多红火亦无济于事,暖不起这腾云驾雾天地一色,要不是身旁时常尚在一些曾经的旧人,白久每天醒来,都难以觉得自己是活着的。
“主神陛下他,今日一早散了早朝便有事出宫了。”刃衣知道她脚下着急,不再啰嗦过多,边看着她脚下抬头低头的回话,“现下时候还早,内务府的总管公公差人送来了好多新鲜物件,都是主神为您挑的,里头还有不少上好的补品珍馐,对您的身子是极好的。”
“世上所有千金难买的东西,应该都在我这以婵宫里头了吧……”白久自嘲苦笑,撒开了刃衣的手,提起裙摆,步伐稳快如常,入了门槛进去。
“参见善容妃娘娘。”两道排开,皆是整齐列队,紧凑密麻的宫人宫女,跪地行礼。
“你们又是从哪来的?”白久眼前看着更是闹心,皱眉大声道,“你们若是还把我当成娘娘,就从哪来回哪去吧,林竹和蕊儿在哪?她们人呢?”
“善容妃娘娘还是别为难我们这些宫中的奴才,都是奉旨前来,是没有退回去这一回事的。”板板正正的牛头不对马嘴,拿着鸡毛当令箭,“您身孕月份大了,还不能久站在外,小心风寒累着身子。”
“他派来的奴才是好本事,本宫问你话都回不得了,是吗?”白久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抖擞头脸发昏发热的眼眶通红,扶着宫门柱上,死撑起了身板。
她确实身体左右不安,心绪不宁,久病成疾,心病难医,说起来她是个天塌下来,见了自己有了伤出了血眼睛都不管眨一下的人,轮到今时今日时过境迁,竟也有这等脆弱不堪的时候。
雨师赋也好,白少君也罢,她再怎的气不过亦只是表层而已,不会吃心到毕生难忘,正如她记事以来,从未做过后悔之事,百密一疏,病入膏肓时,定是因小失大造成的无法挽回之过错。
而当下此时此刻,这鹤容世才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祸害,将他千方百计,不惜改名换姓的跟她逢场作戏,连哄带骗的将她诓进这活人不存的中州,锁进了不过曾经余温消散无影的宫壁之中。
外界再怎样七嘴八舌,她都可作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鸡鸣狗吠,但在此看来,他鹤容世一声不吭,连刃衣这等前朝女官身份的,都不明白他出宫是为了什么正儿八经的事。
亏刃衣还是自己身旁的人,都不能打听到个影子。
可悲可叹,眼前这帮以他名下分派来的人,成群结队,生怕她再在他顾不着的地方动弹个一步。
“说的可真好听,要是真的怕掉脑袋为了我满口担忧,怎还会在这跟我相逼呢?”白久震怒之下,疑心直言相击,“想还要自己头上脑袋的,统统都给我让开!”
白久生怕再晚上个一时半刻的,自己就失了手足终成残废。
袖内的短长匣子随波逐流的上下重落打击,她才忽然顿悟,段印染着实不是信她,而是将她作为另眼相看的奇才,得以重用。
二来是想让她安分些许,才以至用,省得成天操心些鄙薄无聊的恩宠,少了这点东西那点看望的急火攻心。
到底怎样意思万般思绪在其中,她现在猪油蒙了心无暇顾全大局,闲情逸致的多思多想再做体谅。
鹤容世一出去,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的,她竟然到了现在都一概不知,火急火燎的推门去寻蕊儿和林竹的影子,闷声不吭不叫喊,自得自己去看。
“娘娘您慢些,蕊儿和林竹姑娘方才并没有跟着我们过去拜访太上皇陛下,想必一定是回来了以婵宫,不知道在哪干活,您传唤一声就好。”刃衣竟也赶不上她,在后头大喊,“您再这样跑下去,身子会受累动了胎气的!”
“娘娘?我方才好像听到了刃衣的声音。”蕊儿的声音是藏在一处高茵木丛出来的,白久伸手去扒开,才看到了她们弯腰弓背的,是在打水。
“参见娘娘。”林竹转见着白久的一瞬竟觉得与寻常不同,此感是撞上了心头,但终究其理是免不了还是行礼盖过。
“娘娘您这是怎么了?衣衫都乱了,像是跑过来的,您身子可不能跑啊!”蕊儿首当其冲,来到她身旁扶着她想着往回的寝宫走去。
“你们都退下吧。”白久照旧一把推开,抬目看了眼林竹,“你跟我过来。”
“是。”她跟着抬头行走,跟在了白久身后。
“把门关上吧。”白久的步子总是无可阻挡,与众不同,说是连蹦带跑的,却是怎么看都看不出是拿用力飞快了。
跟着她后边,林竹不但是脚上功夫,亦提心吊胆的顾不上看路走马观花,神不知鬼不觉的还不知什么时候进了寝宫内,转身摸索着门栓挂好。
以婵宫内外坚固,门窗无一是这样的重工打造,多少是鹤容世这十几年来,在外唯一回到中州的要事,自然是无坚不摧,毫无挑剔的。
“你是有什么话,什么事要跟我说吗?”林竹瞧着她仅是身影就变得让人感官与寻常时候不同,绝烈清淡,就算头上的银饰望去诸多,也遮蔽增添不了半分华贵喜色。
“我带你出来的这一日,你觉得这里,好吗?”白久抬头,张开双臂旋身转过,双眸定在了她身上,此举突如其来形如发疯,好在她从心而露的心如止水,好比是同戏子动作一样儒雅的。
“金碧辉煌,的确是我清贫一辈子都求不来的。”林竹如是答到,眼看着白久,伶俐至极的眉眼嘴角偏然有了些笑意,“之前是我冲动,我替叔父给善容妃娘娘道歉,如此大恩大德,我林竹当牛做马,来世报完。”
“大恩大德这四个字,我曾经听了二十年,那是我的一辈子。”白久憾然嗤笑,甩了甩双袖,往林竹面前走来,背光而行才见她方才双眸是寒光无影,“所以我现在,想让你替我待在这继续下去,你是否愿意?”
“为什么要离开?你们中州的规矩,我看看就好了,真要做的话,是做不来的。”林竹全身才透得她些许悲凉,“我明白这里头的人情世故,是和尚海城一样的,你不想待在这,可有想过你肚子里的孩子?”
“……”白久颓废得不予理睬,低了眼睑垂眸看地,行尸走肉的形貌,好是在大失所望林竹竟然拒绝了她,好半天无话可说,悉听尊便。
“我林竹虽然是市井出生,但绝非是得偿欲占所有的人,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完整的人,他要有父母傍身,否则你先前为何会在尚海城时耀武扬威的,突然决定说要离开?”林竹见她木然模样,心绪顿时激荡而起,说了一大席话,抓住了她的手腕,“白久,你好大的盘算,自己始终折不了身,便让我来替你做这吃力不讨好的后事吗?!”
“不,不是这样的……”白久恍惚间脑袋昏疼,扶着脑袋往后倚靠在桌边,才算安定了,罢休停下。
“你怎么样?还好吗?”林竹这才知道她方才像是被什么怪力乱神附体,无怪乎她刚刚行为诡异,“刚刚你身体……”
“你应该很早就看到她了。”白久再度睁眼抬头,恢复了清冷平静的常态,“你方才所见的她,是一个和我志不同道不合的另一种意念,是我跳海之后,沉积十几年的不死妄念,到了现在时机成熟,她已经和我分割独立,时不时会趁我激动时出来,妄自伤人。”
“……原以为你只是肚子里有个人,还真想不到,你会经历这么多,多到影响至深,神形俱裂。”林竹若不是亲眼所见,也不像是个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都人,“你刚刚去那个太上皇那边,是又遭了什么事,以至于她出来大喊大叫的要抓着我,将我关在这,迫不及待的想要逃出去?”
“大喊大叫还算好的,上次的时候,她捅伤了鹤容世,得亏他让我捅上这一刀,把我给揪了回来,否则我早就不复存在了。”白久看外的自嘲唏嘘罢,双眸定睛在了林竹身上,“她刚刚所说的,你可都听见记得?”
“那是当然。”林竹走近点了点头,稍俯下身附耳细听。
“我拜托你所要做的事,如她方才所言,话糙理不糙的,替我在这守上一段时间,我得出去止息一件大案。”白久低声细语,“这期间,你一定要时刻称病,一步都不可出去。”
“你可有想过主神,他要是砸门进来,我有什么余力来抵挡他?”林竹提到鹤容世不忍发怵,说不上来这是个怎样的人,只知道他深不见底难以探测。
再看他回中州的行驶毫无章法的以暴制暴,想来也不是什么好相与的,林竹只愿自己一生和这人毫无干系,安稳度日就好,知足常乐。
“想不到,你也会怕他。”白久惊诧,意想不到一直临危不乱的林竹,能有缩头缩尾,瞻前顾后的一天。
“善容妃娘娘抬举我了。”林竹气急败坏,起身抱胸冷然道,“你以为人人都是你一般,不怕死又得这样杀人不眨眼凶狠人的心的吗?”
“怕死,这是好事啊。”白久刚出此言话落,林竹也不屑再理睬,有个一时半刻的不说话,顿在了原地。
她双眼是一时半会移不开白久了,诸多疑惑凝视着眼前人,看她端着大肚子宽大裙摆披在身,从容不迫行走平稳,顿时也看不出她心里到底在求什么想什么了。
行一步算一步,也怪不得她患得患失,神志不清,刀子未能人人都有受,感同身受世间从无有,悲天悯人仅为奢侈闲散所发闲心,真入了尘世,能独善其身已经是万般难得。
善之一字可无有,保得其身自聪明。
如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行,她白久现下是把她这颗深山老林,无人问津的高竹再寻了块地扎根入土,安稳长存,不失为老谋深算。
“咻——!”林竹此刻静心如斯,方好听得耳边一声风梭疾来的摩擦烈响,猛的转头一看竟见尖锐长驱驶来。
“当心,快闪开!”她脚下跳起飞身旋转,扑倒了白久撞到了一旁的凳子腿边,“啊……嘶……”
“崩!”箭中一去不回头的击进柱中,入木足足有半寸多。
“没事吧?起来坐会。”白久也不悠闲就此罢休,安置好了林竹坐着,才去拔下箭矢,“这是谁的信矢,生怕我没这性命得知吗?”
她看的仔细,箭头上的余出纸张顺手拔出,默然打开得知上头所写的详细,白久嗤笑不成声。
“这下好了,好事成双,我这下是真的伤病,省得去装了,你又得了什么天上掉下的馅饼,竟能如此高兴?”林竹闻声抬头,方才并未看见白久脸色,当是不明所以的问。
“他这睚眦必报的性子,生亏之前回了中宫,忍得好苦,原来是出去做了这等见不得人的事。”白久自言自语,道不详尽,但却喜色过悲,林竹明白她又是为何所动容了。
“我这点伤躺一躺就好,倒是你,想好了怎样金蝉脱壳了吗?”林竹也不哪壶不开提哪壶,能让她尽快出去,了却心结,办成其事,或许就会好些了,“我可不想什么都欠你的,你身上还有着孩儿,必须让我知晓,你走得是否安稳才行。”
“我打算去找一个人。”白久收好了纸条收入袖中,“你是真的想好了,替我待在这?”
“再在这磨叽,小心再有什么机关暗算过来,我可没这力气替你挡了。”林竹答非所问,却字字在理。
管不了是蓄谋已久,还是一时情急,林竹只想让她尽快逃开。
方才那一下挨的是自己,亦是松了口心软了,不再多说什么。
白久默不作声,开栓迎面而来微风大噪,如刃刮来,胜在了无形之躯,任他疯狂亦无济于事,安然无恙
“唰——咻,嗡!”经羽白刃掠刃为风,力穿非溅起,狂风少许海水成浪旋围,鹤容世在其中抡起长鞭,见缝插针极快横扫而过。
“哗!”刹那间浪静悬在高空停滞有形,剔透与世同止,鹤容世手再度落下从头斩尾,再抬起收器。
“啊!”徒有三三两两还守在岸边,扣押着黑帮人众的民军隐约之中,听闻不知谁人一声惨叫破了寂静上下一空,直上云霄破海。
喊叫者不知者谁,听讯者酣畅淋漓,止于终了,戏中无人惊动,戏尾高声叫好,以发浑身解数,痛快而已。
“太好了,我就知道这火鸟看着厉害,实则只不过是个不经打的纸老虎。”其中有人先下定论,高兴得跺脚,“你们这老大也算惨到至极,非要逆天而行,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别给我在这胡说八道,我们老大分明还没落下,指不定是你们那主神吃了我们老大一记重击的嗷嗷大喊!”更有甚者蹲在地上拔着脖子,瞪眼探头,“输不起就输不起,别想在这着急赖人。”
“轰——哗!”方才反驳完毕,天顶打出一平荡漾,一束红火直直砸入海面,激荡三尺高后,淹没闭合在水波逐流之中。
“唝!”没了水浪,分分明明悬在高空的鹤容世飘浮下到海面前,单抬一手又加了道四方金光的咒印法阵禁锢,移形换影间回到了码头,踩到了水泥地上。
“主神陛下。”守界使拿起长矛先行跪拜行礼,民军断断续续随后。
“给我死守这片海域,但凡听到一点响动,打回去就好。”鹤容世轻飘飘间好声嘱咐,拿起手掌内尚在飘浮的几根冒火的金羽毛,端详轻笑着捏作灰飞。
“谨遵主神号令!”高声震撼齐应。
“怎么还在押着?都是些过目的无知者罢了,放他们走吧。”鹤容世转过头又是另外一副嘴脸,仅是意思着笑了一下,转身就消失而走了。
“刘子行他人呢?让他过来见我!”江柔茵这会子跟着被带进了一方小小茅草房内,见空无一人,简陋得只有一张椅子一盏灯,砸门大喊大闹。
“江姑娘,你先委屈一会,我们刘队长也是奉命行事,你身份特殊,组织要盘查也是避免不了的。”在外站岗守门的小民军还算好心的,还会劝慰她几句,“你来的突然,里头也没什么准备的,要是缺什么你可以跟我们说,我们都会帮你拿来的。”
“都是些假惺惺的货色,别以为我不知道刘子行他是故意的!”江柔茵狠踢了一脚老旧木门。
“江姑娘,你和刘队长之间,或许都是误会,你放心,我们民军是不会误会任何一个无辜的人的。”在外的小民军依旧话不投机,八竿子打不着边服了软。
刘子行是民军创立之初的老军人,威望声明无一坚不可摧,要是说他以前还是从云苏皇宫出来的,见多识广,无所不知,常言道他阅历颇丰,亦是免不了身上自有过节。
只是江柔茵是个女儿家,民军再怎样行事都是讲良心,不会想什么就拿出来说,刘子行偏生对她态度是陌生又熟悉,爱搭不理,免不了让人匪夷所思,多生猜疑。
“我来给江小姐送些干粮,你们先下去休息会吧。”刘子行的声音沉闷纤细,江柔茵一听便知的回头往木门前靠近。
“是,刘队长。”两个小卫兵应下,脚步声沉重远去。
“吱——嘎!”门被外拉开,江柔茵转头回望,冷目一哼:“你倒是还敢来。”
“的确招待不周,但江小姐这几年所犯下的事,也对不起太好。”刘子行亦是阴阳怪气,“开门见山,以前我和你之间的那些事可大可小,早已算不得是个过结,如果你能配合我们这次的调查行动,让江忠正归顺我们,合力抵抗外敌,你身上的过往一切,我都可忽略不计。”
“原来这尚海城的特工刘队长,也会有这样求我的一天。”江柔茵拒了他的话,“记得那晚我为你百乐门安排了活计,你迟迟不来,我还以为你死了,不曾当回事。”
“你不想配合,也会有另一条路,这由不得你选。”刘子行忽而正色,“你现在从这个门出去,逃出中州,你若能在外活上个一年半载的,大可有朝一日回来踩我的头。”
“你这又是在关心我?”江柔茵看了眼桌子上,他端进来的寻常菜食,倒是像见着了寻常踩踏着的地上草芥,一把推开散了一地,“刘子行,我告诉你,我饿死在这也不会求着你来救我。”
“那就随你的便,能死在这也不冤枉你。”刘子行点了点头,手插进了裤腰带,上前掐起了她的下巴,左右狠拽的端详,“反正你这张皮就是你的体面衣食,能走得干脆些,也能对得起你那倒霉父亲。”
“哼!”江柔茵双眼坚利,有坚贞不屈的炬如火光。
“江小姐的表面功夫,如火纯青。”刘子行抓起她的袖子,重重往地上摁去,恰好抵扣在了被打翻的一地饭菜,“你得用它洗洗脸,好好得到一些清白干净。”
江柔茵被他这一番极快动作弄得口不能言,任由刘子行将她拽撕下来的一手小点衣角甩到她脸上,任由她皮肤参透空中,暴露无遗。
“善容妃娘娘,南诏国的那兰公主,先帝之女的手足姐妹,过来造访了。”蕊儿被逼的在外跑进,见着寝宫门开着,开打进入传道。
“她也算是我阿姐,麻烦她先在外等着吧。”白久在床边回头一应,塞好了林竹的被褥,天衣无缝,看不出半分其他不对。
再者林竹是平躺,身形上揣着个枕头,看上去就一样了。
“是,奴婢这就去转告。”蕊儿着实着急,不怎么细看转身回去复命。
“你去吧,回头蕊儿这边,我自有办法。”林竹半晌,同她道出了一声辞别。
夜阑卧听风吹雨,风萧萧兮易水寒,不复还亦生别离,执意一念之差,能成能败,总归尘。
离也痛,聚也愁,于是分离,今生此缘尽,不得求,各生欢喜。
——————————————
微末:
微末:对不起大家,我劳动节太忙了,只能青年节给大家助助兴了
微末:剧情进入终极的白热化阶段
微末:感谢等待陪伴哦!
明堂拾经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贝利亚:她终究不属于我
- 简介:"我的心如同镜子一般,碎了就拼不回来了,只剩下满身的裂痕、碎片,你终究还是选择他……终究不属于我,真可笑啊…………″[文笔很烂,不喜勿喷]
- 1.2万字2年前
- 斗龙战士之凯风和百诺
- 简介:爱情侣装,总共9章。
- 0.0万字2年前
- 无限流:童话乐园
- 简介:【1V1双强+无限流+白切黑】别人都在认真逃命,童安真把它当个游戏玩。
- 8.2万字1年前
- 罗里奥的异界
- 简介:冷风吹进阴暗的房间,烛火摇曳,影子晃动,他端详着陈旧的古书,深褐色的书皮上写着两个字——异界
- 3.4万字2年前
- 炮灰师兄他心口不一
- 简介:炮灰想逆袭就这么难吗?是谁阻碍了他摆脱炮灰之路?温点幽灵魂发问。温点幽作为百年难遇修仙奇才,不曾想挂在飞升临门一脚。离谱的是他脑海里还多了一个声音,自称是炮灰拯救系统。只要他认真完成任务就能继续修仙。然而,他分明完成了任务,系统却说出现了“意外”。两次任务皆出现意外,温点幽怒。第三次任务,系统笑呵呵地说最后一次,这次简单。只要确保主角跟他都活下去,顺便走完主线依旧存活,他就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不用做炮灰了。系统说这主角九尾狐狸表里不一,小心他背后报复。温点幽每日过得战战兢兢,一面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一面又担心他死了。只是,这狐狸看他的眼神怎么越来越奇怪?某一日,燕照影摇着狐狸尾巴邪魅一笑,“师兄,表里不一的是谁?”表面冷淡内里话痨温点幽×白切黑燕照影
- 7.4万字2年前
- 你们能不能正常一点
- 简介:万人迷无cp向,男女通吃。榛子进入异能学校的那一天,发现了……昔日的阳光女同桌变成了高冷大姐大,只不过还会在自己面前撒娇,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用警惕的目光看着所有人。校园温润男神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我其实对你一见钟情了。"以及高冷的学弟会默默地在放学路上陪着她一起走,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攻击。超高智商的特工弟弟,会时不时向自己求抱抱,尤其是分化成o的时候。对此榛子表示"你们能不能正常一点啊"
- 0.7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