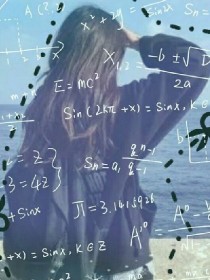第一话 谈资
每到农闲时光或是茶余饭后,七家镇的街头巷尾和门口院旁总会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谈资交易”。那些“东家长,西家短,儿媳妇挠了公公脸”的重要情报就靠着这种“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增殖繁衍。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一次又一次的交换中湮没,或是随针线纳入了老婆子为老汉做的鞋垫中,或者随着老汉嘴里叼着的烟卷燃尽飘散。
自从秦金泰醉酒归途水中横死,七家镇庄户人家又多了一项重要而长久的谈资。因为秦金泰一死,秦家绝户仿佛成了不争的事实,他们喋喋不休不厌其烦的说着秦家往日的兴旺,感叹秦家现在虚浮的荣光,虚幻的想象着秦家未来的悲凉。就是这样那样的几句话,再填上几声哀叹作为佐料,总能够在他们嘴里咂摸好久,恨不得像咬了一口西瓜似的,非要把那汁水咂干。是啊,谁能想到兴传四代的秦家,会落到这种下场呢?那些庄户人一边说着秦家广阔的田地,壮实的牛骡,生钱的旱烟生意,一边把牙花子嘬的咂咂响:可惜咧,都是人家的了。
七家镇的大多数人家对秦金泰并无好感——即使是秦家的本家人或是亲戚。这种反感厌恶除了源自于庄户人对于败家子与生俱来的鄙夷,更多的是对秦金泰横行乡里的愤恨。那些庄户人当着秦金泰的面称呼他秦爷,背地里却叫他的小名“栓狗”。
秦金泰之所以叫栓狗,还有一段缘故,秦金泰她妈为了生他一只脚跨进了鬼门关,整整折腾了两天,到第二天抹黑才生下来。那时候庄户人家正开始做饭,被夜色染黑的空气中,苞米秸子和柴草燃烧的烟火味和饭菜的香味混合在一起,秦家上下谁还顾得做饭呢,院子里的狗栓了一天,看到接生婆子来来回回屋里屋外端个盆子跑,以为是来喂它的,那狗先是汪汪呜呜,后来三挣两挣,脖子上的绳子撸了扣,奔着婆子就去了。婆子正往屋外走,借着窗户棂子透出的烛光,就看到那狗朝自己扑来,那婆子妈呀一声,扔了盆子就往屋里跑,一边跑一遍叫:“秦爷哎,那!那狗!那狗开了!栓狗啊”。
婆子口中的秦爷是秦金泰的父亲秦培宽,这时候正在北屋九百八十遍的急踱着碎步子嘬着烟袋嘴儿,听到婆子喊叫,以为自己老婆生了,跑出去才知道狗开了,便又急又气嚷道:“你急个啥,不是没咬到你,那边还生着孩子呢,就顾着栓狗!快进去快进去!”
正说着,屋子里传来了孩子的啼哭声,谁还顾得去栓狗呢,都跑去东屋看孩子去了,那婆子慌里慌张却还不忘了打趣:“狗不开你不来,你倒怕狗咬,狗开了顾不得栓了你跑出来了”。也是觉得贱名好养活,于是秦培宽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栓狗。
谁能想到,当年的狗确实没咬人,但当年的秦栓狗却长成了一条咬人的饿狼呢?
这多少算是秦培宽的罪过,常说“惯子如杀子”,也是秦培宽太惯着秦金泰了。可这也是常情,秦培宽的爷爷有弟兄五个,活到成年的只有三个,也是祖门无佑,三个儿子却落得一个无儿一个无子,只有秦培宽的爷爷生了两个儿子,秦培宽的父亲叫秦树义,排行老二,秦培宽的大爷叫秦树德,生的身高体壮,可结婚一年不到,竟然得了“瘦病”,先是能吃能喝不长肉,后来是不吃不喝成骨头,那病也怪,全身骨头像被敲碎了般疼,没挨过一年,就死了。
到了秦培宽时,秦家已算是单传两代,虽然靠着两辈的积累和祖上的横财,已在七家镇富名远扬,但秦培宽却丝毫没有富人的酸架,不光秦家雇人栽烟掰烟的工价比他处高许多,北岭百八十亩的耕地的租金也比市价低半成。从沿街的叫花子到贫苦的庄户人家,哪个没在手短挨饿时受过秦培宽的接济呢?
也是盼什么缺什么,秦家算是两代单蹦,到了秦培宽这里,做梦都想抱上儿子,最好是一窝儿子。可秦培宽娶妻五年他老婆的肚子依旧没有动静,五年来七家镇的菩萨庙年年受秦培宽的善荫而粉刷一新,土地庙里塞满了秦家的供奉,可他老婆的肚子就是没有动静,第五年本来秦培宽动了休妻娶小的念头——秦家香火总不能断在我这吧?可是偏偏他老婆那棵老艾蒿还了阳,生下了栓狗秦金泰,秦培宽如喜从天降一般,一次就免了北岭八十亩佃农一年的租子。可惜,秦婆子的肚子再也没了动静。
独苗秦金泰,秦家上下谁不当宝贝供着?从小秦金泰毁屋坏舍偷鸡杀狗,秦培宽不知赔了多少罪,为他掷骰子推牌九,也不知搭了多少钱。多少次秦培宽下狠心教训儿子,可儿子秦金泰打个喷嚏,这个当爹的就怕震下房梁砸到儿子,所以到最后也不过巴掌扬起来,蜜枣喂下去罢了。
就这样秦栓狗浑浑噩噩长到二十岁,七家镇谁家苗毁了,牲畜被毒死了,不用说,肯定是秦坏狗干的,其实秦金泰也不为了什么,玩呗。
七家镇的人谁也没想到,秦坏狗就这样被水鬼拖走了,做了半辈子好事的秦培宽就这样成了绝户。
七家镇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地心人
- 简介:28-29世纪的地球已经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星球了,但人们依然没有放弃对外星人的探索。但一次意外的事件使人类探索的方向从太空转向了地心。
- 0.4万字2年前
- 过去,未来.com
- 简介:18岁,本应该是所有女孩最美好的时光,可当沈若兮的十八岁生日来临时,一切,翻天覆地……
- 0.5万字2年前
- 叶罗丽精灵梦之仙境最强公主
- 简介:王默竟是仙境的公主,会发生什么?
- 0.0万字2年前
- 一夜變狐妖大人
- 简介:人人都說我冷漠,但你們不了解我
- 0.0万字1年前
- 喝多_d392
- 简介:嘎嘎嘎嘎嘎嘎他
- 0.1万字12个月前
- 吾凰在上(现代版)
- 简介:一个宅女想买新出的游戏机,然而,她没有钱买,所以在到处的找工作!而当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作时,却落入了霸道总裁的套圈,就这样经历很多磨难,终于落入爱情的河中
- 0.1万字1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