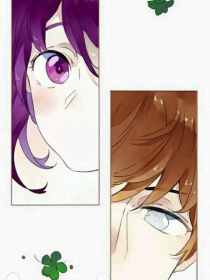我即人民
*没有完结 没有完结
*政治偏执狂是齐时代真实病症名 可惜我未能找到详细记载 很疑惑治疗方式
*“战胜了自己”语出1984
“孟德斯鸠。不要为死者哭泣,为诞生者。”警察找到我时我对他说,血液从我发梢小雨一样滴落,“噢,我忘了你们不可能读孟德斯鸠,人民没有这权利。”
他们把我关了三天,三天,又三天。牢房里很难见alpha,只要我能让自己的信息素被嗅到,便鲜少会有麻烦找上门。每个晦暗的黄昏和灼热的午后,我都隔着栏杆朝狱卒们念诗,拜伦雪莱和济慈,周遭环绕玫瑰花的香气,好似身处保加利亚的山谷。在那些孤寂而漫长的时光里,我烂醉如德尔菲神庙离群索居的祭司。然后有个穿制服的人把我押上法庭,我知道他们给了我最后一点作态的文明:一个申辩的机会。
我总是热爱沿着我灰蒙城市的苍白的街道散步。我总是热爱深夜月光颤抖晚风唱哀歌的时分,醒着重温我生平未见的黄金年代旧梦。我总是流下泪来,代替我不曾出口的真话。我总是个懦夫。
母亲说我孩提时代常常放声大哭。那时我多勇敢,多光辉。我拥有年轻、自由,和所有殉难着隐秘的期望。我是一抔烈焰,为所有被戕害的母体、所有被折笔的艺术家,所有失声的无产者,所有罗马尼亚人的良心向不美丽的世界呼号。
何为懦夫之怒?我决意如向生般向死。
“我委实有罪,先生们。”
我抬起头环视过他们,想,仅我自己能定我的罪。
“我的罪过不在于杀死侵犯我爱人的凶手,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多杀一个。我所犯的大罪与每位罗马尼亚公民相同——未能警惕极【和谐】权主义。不到半世纪前,我们参与了消灭人类历史上最大法西斯政权的战争,许多人的父辈葬身炮火,奥斯维辛被摘下的婚戒依然闪光,纳粹的坟墓至今高耸在我们眼前;这鲜活的尸首和疮痍并不让我们引以为戒,警惕法西斯主义的复辟。正相反,我们冷眼旁观《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颁布,冷眼旁观堕胎遭禁止,在暗处,有更多领主制式的剥削,我们却从未向暗处看。我们以默许权力滥用的方式残害我们的亲朋、伴侣、儿女。我们的经济由尸体堆高,暴君的王座由骨血搭成。我们的同胞流离失所,行眠立盹,苟活过黑暗时代的严冬。与此同时,有人躺在黄金上赏玩我们的苦难。海王星、春天宫、佩雷什宫,它们每一块砖瓦都埋着人民的哭喊。倘若我们真的是合格的公民,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何至于沦落至此?我们的好总统自诩罗马人的后裔,昔日兼容并蓄的罗马人的后裔,拥有最完善的法律体系的罗马人后裔,杀死了凯撒的罗马人的后裔。既然如此,我们比任何人都该深知民//主珍贵,我们比任何人都该深知恶法非法。
罗马尼亚的人民,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正义之师交战,他们必将粉身碎骨。这话是由我们的好总统亲口说出的。现今他转过头来,由革命者变作了压迫者。罗马尼亚的人民,不是齐奥塞斯库给你权力,而是你给齐奥塞斯库权力,人民一旦唱起歌来,暴//政就要销声匿迹。路易十四宣称他即法兰西,不过三次王权交叠,他的后代便在动荡中人头落地;凡尔赛宫光灿无比,也亮不过人民汇流成的星火。君主只能有一位,人民可有千千万,这便是人民的力量。人民可以选择沉默,可以选择屈膝,也可以选择站起来争取天赐众生的权利——自由、平等,博爱。罗马尼亚的人民们,我和你们的不幸是一样的,我也懦弱驽钝,我也缄默无言。但今日我无所畏惧,因为自由之花须染血,因为我死自有后来人。我希望凭我所有的诚实告诉你们,要有勇气,要有希望;人民是被割断头发的参孙,人民是沉睡的雄狮。愿你们觉醒的那日一切归于你们!”
我听到我耳畔喧哗声纷乱。他们要我停下吗?
可我已经沉默了整整十九个春秋。乃至开口便要声嘶力竭。
“这还不够!公民!还不够!我们是为公义战斗!即使解放罗马尼亚,一道贪婪自私、愚昧不仁的壁垒依然横亘在每片沃土上。应该把这壁垒彻底摧毁,让偏见和礼教都土崩瓦解。所以,保持愤怒,一刻都别停!
随便!随你们处置我!枪决我!砍下我的头!把我绑在火刑柱上烧!我要所有暴君的血染红多瑙河,哪怕他的国土只有一间卧室大,到那刻我们就自由了!”
他们没有判我死刑,这恰恰最残忍。
我没能做一个流血的殉道者。
我被关进了市外的精神病院,病名是政治偏执狂。这里很多人曾经比我更勇敢,一段时间后,有人战胜了自己,有人一心制作自己的棺材。
大约几个月后,左臂的皮肉被电流烫焦、我跪在地上翻滚的那天,我看到了我的爱人。
和别人穿着一样的囚服,站在队列里,他深深地,深深地望了我一眼。
还是那副高洁得让人晕眩,又温柔得让人落泪的容貌,用那双比辰星更明澈的眼睛温情脉脉地告诉我:你至今仍是我的骄傲。
第二天午饭的时刻,他借着擦肩的机会塞给我一张纸条,我只敢夜间借月色看。
熟稔不过的清秀字迹,写了满满整张纸。他没死成,警察去搜家的时候发现了失血过多昏迷的他,顺手送进医院了。他一转醒就有人来盘问他为什么堕胎,他回答,我太爱我的孩子了,不忍心让他出生在这鬼地方。
然后他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
所以,他还没好全就被送进来,成了唯一一个omega性别的政治偏执狂。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说话的机会,但已经可以用眼神交流。我一直没有找过镜子,疑心自己早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和当年那个娇柔少女判若两人,但他还是美得不可思议,像日复一日升起的太阳,奥斯维辛盛开的花。
我想起来加缪说的。荒谬当道,爱拯救之。
天道仁慈,恩赐我们一切生平苦难,又给予希望和爱安抚。
曾经有无数个君主,未来也有无数个君主,手握权杖梦着万民俯首,如野兽般互相争夺着蹂躏土地的权力,硝烟未定时下一阵硝烟便燃起,鹰之丘的大绞刑台汇集冤魂的哀鸣,银铸的圣母像上亿次为后世的暴行流泪。
我如今只怜悯他们。
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像我这样炽烈地爱过。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能体会我所体会的狂喜。
毕竟,凡俗千千万,和爱相较,不值一提。
现在是一九八四年。罗马尼亚的黑暗时代。
这时代终要结束,长夜将近总有黎明。
此时此刻,我在疯人院把这句疯话讲给爱人听。
世上所有的河,河里所有的浪花,此时此刻都有爱神新生。
爱神途经多瑙河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重生之校草him暗恋我
- 简介:“等等。”她没有回头“Ceris……”她的脚步一顿,顿时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画面;满地的鲜血,到处都是末影人的尸体……(嘿嘿,这是作者的第二部小说哦,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 4.6万字2年前
- 莉莉丝的私房物语
- 简介:人间轮回几世混,九天玄女下凡尘,贪嗔痴慢尝几遍,才知人间一缕魂,梦中彷徨终未醒,黄粱煮酒酒温温,奈何身去魂还在,望断天涯沦落人,梦里许她千百度,她在轮回雪纷纷,渺渺漫漫春去也,忘川之水溺红尘,你却抬头看看她,她有多么善良人,不信你去问秋水,秋水斜雨雨纷纷。难忘青春年少时,梦中仍见少年人,花季雨季总一瞬,梦中不见栀子花,醒来翻看少年影,醒来空空冷清魂,魂梦不见终长成,中年危机惊扰人,忧愁烦恼如梦令,长成不见少年气,中年难逃庸俗人,不见五陵豪杰墓,堂前燕飞百姓家,写作小说寄托思,思虑不见年少时,纪念心中未爱人!
- 68.7万字2年前
- 不明的血统
- 简介:男主倾酏在高一刚开学时因为容貌,深受女同学的喜爱,邂逅了女主夏沐清,之后又遇到了一些人,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秘密,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少数人群,他们被称为“吸血鬼血统者”被普通人中的一些所视为威胁、异类,不被世界所认可,就连他的发小江英也都牵扯在里面。这也是倾酏的父亲一直对他和弟弟倾尘隐瞒的事,当初母亲带着妹妹倾恒琳离开就和这件事有关,为了安全,他们不得不隐瞒身份,但高中生活也不会再平静。其中也涉及一些亲情、爱情、友情等日常。是GB,可能前期看不出来,但的确是GB文
- 72.6万字2年前
- 永生难忘
- 简介:17岁青春美少女vs24岁巨帅大叔七岁只差一见钟情小姑娘的暗恋之旅就此开始......遇见他之前,我觉得一见钟情是胡扯,遇见他之后,我打脸了。“要在我生命中待很久很久,好不好”“你不懂”念念不忘,死也不忘,永生难忘。......年少时的我们,以为说过永远,就真的可以永远。后来啊,我淋过很多场雨,仰望过很多地方的星空,却永远铭记最初的那次怦然心动。
- 1.9万字1年前
- 你是我的信念
- 简介:[救赎文]天不佑我,我出车祸了,但是我居然没死,还穿书了!但是!全员be是怎么回事?我既然活了下来,当然要守住我自己的小命,但是反派男二是不是太惨了点林淮,家里妥妥的的富二代,但是一次变故,家里人全没了,让自己的腿也不能走起来,周围所有人都避开他,可是有天有一个小女孩来找救他了,她改变了他的一生
- 0.5万字1年前
- 妍笑砚砚:我是他的全世界
- 简介:明艳美人×温柔总裁女主原型是我的亲亲闺蜜
- 7.0万字8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