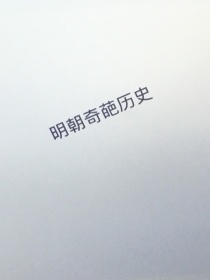第四章 应声而碎
许樾没想到叶浔第二天夜里就来了
彼时他才刚沐浴完毕,换上中衣,倚在书房里那张美人榻上看书。
深秋夜里起了风,院中花草摇动,树木也沙沙作响。书房点起了安神的熏香,几星灯火荧亮。月上中天,越过屋沿。
细不可闻的破空声传来,屋顶瓦砾晃动一瞬。
下一秒,书房门口敲门声传来。
“先生,是我。”生涩且略带西南口音。
叶浔?她怎么会来?
许樾重新拢拢外衣,起身开门。
门开开了,门外是她。
今天没穿黑衣,但仍是一身骑装,雪白色的,外面附着软甲,头发攒成一束,高高扎着。眼里有些血丝,看上去稍显疲惫。
犹豫了一下,许樾侧身让她进去,看她踱步到书桌前,发呆一般盯着那支狼毫。
他合上书房门,倚在门边。
“今天是不是有些忙?”许樾漫不经心问道。
“不算…太忙。”她答。
许樾知道有些事涉及军机,并没有再问。
房里有只蜡烛燃尽,发出毕剥的炸响后迅速熄灭了。那一角失去照明,陷入黑暗。叶浔深夜前来,许樾自然不会叫人来换。
许樾尚未动作,叶浔却先他一步去换了那支蜡烛,燃起新烛。
烛苗缓缓摇动,叶茗清转身坐在窗下那张梨木椅子上,侧脸在窗纸上投出一个黑色剪影。
许樾敏锐地发现她心情似乎不是很好。
“今日想学些什么?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问我。”许樾凝视她,率先开口。
“想先学些日常…用的上的。其实…我能听懂,只是..不大会..讲。”她眉尖微微皱起,回到。
许樾略思索一番,决定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教她常用的语句。考虑到她是将军,可以再优先把军营里用得上的词教给她。
许樾在脑子里顺了一顺,告诉她:“现在我说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模仿的越像越好。”
叶浔重重点头,表情很严肃。
“准备好了,第一句…”许樾开口。
“准备好了。”她立刻跟着念。
念的又快又急,好像有人跟她抢似的。
许樾忽然想笑。
还将军呢,这不小傻子吗。
许樾清清嗓子,再道:“请问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请问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复述声响起,把他的语调学了个十成十。
“学的很像。”他肯定到。“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叶浔点点头,学得认真,灯下一双杏眼大且圆,两只柳眉利得仿佛要刺破灯罩。
许樾继续教下去。
“今天天气不好,刮了大风。”
“今天天气不好,刮了大风。”
许樾对她点点头,继续道。
“我早上吃了米粥。”
“我早上吃了米粥。”
…..
许樾教了很久,耐心到叶浔每说完一句,都要夸上她一句。
就这么一句接一句,他说,叶浔学。
或许是得到了鼓励,结束时,叶浔心情显得舒缓了些。对他道过谢告了别,然后呼地消失在院子里。
接下来的十几天都是这样,叶浔总是晚上不声不响的出现,跟着许樾学上大半个时辰,学完之后再不声不响离开。
这天晚上,许樾估摸今晚叶浔也会来,还提前备好了热腾腾的茶水等她。
但是她没有。
连着接下来的一个月都没有出现。
九皇子那里又换了个新先生,许樾回到书院里教书。明年开春有一场国子监内部的考试,既考策论又考诗词,许樾在国子监任职两年,头回碰见内部有如此正式的较考。
考生范围也严格规定在和他同批进国子监的那十几个博士当中,没有明说,可大家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到底是少年人,许樾并不想落于人后,每天回了家便钻进书房,经常彻夜不眠读书。他师从当朝大家庐阳先生,少时他作文章给先生看,先生总说‘勘有其形,不得其韵’,这两年进了书院,反倒比从前长进些。
许樾一心扑于笔墨,不闻它事。
十一月上旬,京城中流言四起。
流言的版本虽然不一致,但核心内容都是一致的,无非两件事。其一,西南招就的镇远大将军是女子。其二,叶浔其祖为五十年前战死于禄渊的建威将军。
更有甚者,直言叶浔是顶替他人职位,依靠家族关系当上的将军。
起先还只是在世家大族之间传播,当这流言由许樾亲耳听到时,它已经传遍京城大街小巷。
更为糟糕的消息是,三天后,万德四年十月初三,立冬。
天子为首,率百官祭祀,城中百姓可列道观看。
上天没有给叶浔喘息的机会。
她要站在谣言中心,直面万众之口。
那天晚上,许樾终于再见到叶浔。
没有人天生就能成为什么,将军不是天生就是将军,先生也不天生就是先生。
许樾想起小时候,母亲常带他去外婆家玩。外婆家住在红门绿瓦的府邸中,宽阔气派的府墙把街道围了近一半,看着就让人艳羡。
可他们的邻居却只是一户普通人家。
许樾小时候贪玩,母亲每次带他回门,他就跑去隔壁邻居家,和那些小孩子们一起和泥巴,摘果子,编草做的蚂蚱,和他们一起被门口的大黄狗撵。跟他们在一起,许樾总是玩得很开心。
但那只仅限于傍晚时一盏茶的时间。
其余的时间,不管许樾怎么呼唤,他们都不肯出来玩的。
许樾也问过他们。
“你们每天都在干什么呀?为什么不出来玩?”
“我们要练功的。”几个小伙伴异口同声。
“练什么功?”许樾奇怪。
“练基本功啊,扎马步,走梅花桩,每天都要出一千拳呢。”有人抱怨。
是么?那就是练功吗?
可是许樾还是不明白,怎么就能为了练功不出来玩了呢?
有一天他在邻居家的围墙边发现了一个狗洞,他决定钻进去看看。进去之后,他吓了一跳。
小鱼,那个比他还小一岁的小男孩,头上顶着那——么大的一口缸,缸里装满了水,就那么站着。还有昨天和他一起抓蜻蜓的那个,在一根根木桩上走来走去,那些木桩都快有小树高了,还要不停地往上走。
好像是踩空了,他噗通一声从上面摔了下来。许樾眼睛都瞪大了,一定很痛吧。
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小小的男孩,很快的挣扎着爬起来,一言不发又重新走上那些木头桩子。
整一个下午,他看他不停地走上去,摔下来,走上去,又摔下来。看他在太阳下皮肤都晒破,看他满身的泥水,看他想喝一口水却因为表现不好被大人狠狠地骂回去。
原来是这样,原来这就是练功。
后来外婆家不住在那了,他也再没见过那些孩子。
只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那个孩子就那么面对着他,很乖巧道:“不用担心我,我不痛的。”
很久以前看过的画面仿佛与眼前的重叠起来。她带了一身酒气,那么站在院子里。轻飘飘看过来,好像很委屈似的。
那么现在呢?你痛吗?叶浔。
过去的二十年间,你是否也像那个可怜的孩子一样,痛了要说不痛,累了也说不累。有没有人问过你呢?
许樾很想开口,但他长了张嘴,终究还是没有发出一个字。
叶浔心情很闷,很多事在手下人面前说不得,也不知道要往何处去。
漫无目的的走着,不知怎么就到了许府的府墙边。叶浔抱了一小坛蜜酒,就那么轻而易举的翻进来了
许樾就站在廊下,她一眼就能看见。
人逆着光,像影子,像小山。等她走进两步,面容才显露出来,眉是青的松,眼是凌的波,一眼即可见底。那么看着自己,很怜悯的。
已经忆不起是多少年前,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多少双眼睛,也是这么看着她,仿佛看着一只弱小的什么。
已经不再是了。
她的身量变的很高,她的轻功如今世人难敌,她军功赫赫,不用为了一口吃的去和野狗搏斗,也不用为了活着每天和别人拼杀。她已成长为一个很优秀的人。
“哗啦”一坛酒掷地而裂,红色的坛封被醇酒浸透,字迹随着酒液晕出来,月光下反着光,成为一面酒色的镜子。
“不要再这样看我。”她利落的转身飞跃,侧脸在视线中一划而过。
酒香味飘满了庭院。
挽弓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庞毒:小楼昨夜又东风
- 简介:【雪梦】:雪楼凝芬芳,梦里花飘落{本书已签约,禁止转载,禁止抄袭,禁止效仿剧情}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故国,我还有吗?自从毒族灭亡的那一天起,我的命运,也许就交给他人了。落身为奴,遭到不公的对待,自己最好的姐妹的背叛......记住了,你们从我身上拿走的,我不仅回拿回来,而且,还会让你们,双倍奉还!———————————————————————【雪梦文社&盗版家族】江茹绫•执笔
- 4.4万字2年前
- 从一而终,长相厮守
- 简介:一界神童小小年纪就被誉为上神的陆怀安原与五大圣兽族的飞鸟族的小仙主有婚约。无意在仙山修炼时却遇见了身为神鹿的沈月。倔强的他,起初只是因为觉得自己觉得沈月好欺负,整天就想逗他。却发现自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经过一些事,与沈月情投意合。为了和他长相厮守,怀安向帝君拒绝了与鸟族仙主的婚约。众人都极力反对反对。两人又该何去何从
- 3.1万字1年前
- 阿肆肆
- 简介:“朕一觉醒来,本以为会在阴曹地府,结果朕眼前为什么会出现两只毛茸茸的小猫爪,朕.....变成了一只猫!!!”——玄烨“能再次见到孤的小四孤是很高兴的,但是为什么孤的那群怨种兄弟也出现了,而且还跟孤抢小四!!!”——胤礽“呵,只要我这个四哥最爱亲亲王子在,尔等终究上不得台面”——胤祥..........总结“小四/四哥/禛儿你到底要谁?”——爱而不得低头扶额“朕可以说朕想要自己吗?”——愿独自美好
- 0.0万字1年前
- 明朝奇葩历史
- 简介:每个朝代都有自己不同的风采,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么明朝的历史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相信有不少朋友并不了解明朝的历史,甚至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外都不认识。我之后还会出其他朝代的历史。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虽然说只是枯燥的历史,但是我的笔锋也一定会有所幽默感。还望大家收藏❤,我的方位是历史军事史,但不要因为这个枯燥的名字就失去了兴趣八
- 0.4万字1年前
- 穿越之陌上花开之圣铭玥夜九殇的爱情
- 简介:。。。。
- 0.3万字1年前
- 徒弟要黑化了
- 简介:前世她总是对我冷嘲热讽,不断打压我,只怪我有眼无珠认错贼人,可最后替我挡剑也是她,伤害我也是她,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放手了,如果错过是为了下次更好相遇,那重生再也不会放弃你了
- 9.9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