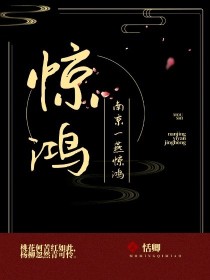四
时逢夏初,在当时却是常见的冷夏,阴凉的空气流淌在树林繁密的山间,沿着这座山的石头小径一路向北,便是久春国境内有名的禅宗古寺。
这一晚,寺庙里的小和尚端着一碗热茶,行色匆匆地穿过佛堂的正殿。晻晻暮色中,十一面千手观音金像上的烛光浮现出来,富有神性的庄肃模样俯瞰着殿前苦读的修业者。
听闻那位在此间进修的少年最近害了下痢,主持禅师吩咐予些热食,其居住的茅庵多日以来房门紧闭,只有小和尚一人因为运送食物和水来往。
能享受着这般待遇,又有贴身护卫跟随,不知究竟是哪一家大门户的公子少爷。
小和尚暗自思忖道。
他把茶碗放在茅庵的门口,屋内即刻传来响动。前来应门的是那位少年身边的青年护卫。或许是由于光线幽暗,这人的身影站在门口像一座漆黑的佛塔,加上面目上的疤痕,光是看到都会倍觉可怕。
“天色已晚,还劳烦您赶来,实在万分感激。”
那人谦逊有礼地答谢着小和尚,在主上卧病的这些日子里始终如此。
通常看到这样的家伙,人们习惯上赖于直觉,以外貌来臆测其跋扈粗鲁的性格。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此人谈吐举动彬彬有礼,甚至于谦逊到了低调的程度,应是受到过相当程度上的教育。出于这样的反差,寺庙里的众僧尼对这对主从的出身心生好奇,私下里也曾有过不少议论。
除却这一点外,困扰这位杂役小和尚的还有一件事:那位少年已经卧病三日,这期间却不曾有医者出入这间茅庵,也从未有药物送来。就这一点来说,实在很不寻常。
趁着大个青年俯身将茶收入屋内的片刻,小和尚抻长了脖子往他身后的屋子里张望了两眼。
屋内的视野阴暗,只能隐隐看出不远处的地板上有一堆摊开的布带,上面黑色的污渍像是血迹。
若是痢血,可就是不得了的大病了。
见此情景,小和尚不由得大吃一惊。
门前的青年觉察到了他的视线,立刻抬起袖子挡在他面前,客气地解释道:
“大人痢病未愈,此间不便示人,还劳烦您回避。”
当晚,小和尚将此事告知了禅师。翌日早晨,禅师前往茅庵查验此事,经过正殿时,却惊讶地撞见那位少年与其随从正细致地擦拭佛像莲台,手脚勤快丝毫看不出病重的模样。当然,茅庵中那一条在小和尚的描述中血迹斑斑的布带也不见分毫踪影。
对于此事,少年只是笑侃自己几天前吃生米坏了肚子,折腾了两天总算排净了秽物,倒也不至于到痢血的程度。
他说的不假,若是那般严重,不要说现在利落地清理台座,连站立起来都是问题。归根结底,想必是那杂役的小和尚在昏暗的光线下看走了眼。老禅师在这之后没有深究,这件事也就渐渐被寺院中的人所淡忘了。
苇名的酒宴不分级别座次,招待的饭食也并非什么珍馐佳肴,充其量不过是战时的口粮装在稍微漂亮正式一点的碗中罢了。众人一进到公馆内就争先恐后地占领位置,足轻大将竟与高官同席而坐,在他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失礼事。
“那边的久岛大人,没想到除了武艺高超之外,竟然能用糙米做出这样的饭团,真是绝顶的美味。”
发出赞美之词的侍大将呵呵笑着往嘴里塞着饭团,这人口音挺重,语速又快,饭团上的米粒在他边吃边说的时候掉进了喉轮铠甲的缝隙之中,那样酷似山野浪人般不拘小节的吃相,让旁观者一时不知该说是豪迈还是粗野。
“呀!有着这等才艺,要是有久岛大人这样的男子汉作乘龙快婿可就太好啦!如何?吾有一小女,恰好已到婚龄,吾愿为大人保媒拉纤。”
面对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的武士,宗马推却道:
“承蒙好意,但在下先前在久春城有一心仪之人,只是尚未能相互表露心意。况且我等主从居无定所,如果仓促答允下来,怕是会怠慢了令爱。”
“唔...大人已经有心上人了啊...不过,既然只是有缘无份的话也不可强求,但如果大人改变心意,考虑一下吾的这个请求也不是不可以。”
吃了瘪的武士撅着嘴,这人虽言行粗鄙,却也不是胡搅蛮缠之辈,对此宗马只得报以歉意的颔首。
另一方,鉴于几日前的失态,佐藤主从也想借此机会向那位少城主表达歉意。于是傍晚时分差役人送去请柬,但始终没有回信,这让义典心中有些惴惴不安。
"不用担心,你再怎么巴结小鬼也是没有用的。"
酒宴始酣,一位酩酊的青衫武士这样嘟哝道,从衣装来看此人是早先与宗马较量过的苇名道场的武者之一。
此言一出,不仅佐藤主从为之愕然,周围的武士的注意力似乎也被这句放肆话所吸引,一时纷纷放下了手上的碗箸,将视线投向这边。
"说什么寻求'不死',那是邪道啊!连剑术也是,苇名流的一招一式都没能习得,反而使用着异端的招式!"
第一次听到"不死"这样刺耳的词语,久岛宗马不由得皱起眉头。
仿佛是要将陈年的苦水一吐为快,面红耳赤的道场武士忽然提高了音量带着哭腔嚷嚷起来:
"说到底大家都是对一心大人心生敬仰才甘愿卖命的,鼓捣邪门歪道的小鬼的人望永远也达不到一心大人的高度!...”
"混账!平四郎你这样也算是苇名众吗?老子来好好教训教训你!把首级交出来!"
一旁座席上的大将勃然大怒,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作势要抓住武士,一时间劝架与帮腔的乱哄哄地闹腾成了一团。
原以为日暮西山的苇名国之所以能够抵挡内府的多次骚扰与进犯,倚仗的就是内部坚若磐石的团结力。但借由此事,佐藤主从当下看清了苇名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团结之下隐藏的裂痕。
道场武士的酒后失言并非只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是代表了苇名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一旦苇名一心撒手人寰,忠于一心一派的苇名众定然会对新城主弦一郎的管辖有所不服,内忧外患之下,只怕苇名会走上比久春更为悲惨的道路。
而在这之中令宗马颇为在意的,是武士在牢骚中无意透露出的"不死"的字眼。
早些年间,在东北地区往来的商人们偶尔带来芦苇之地的传闻,起初这类消息只局限于当地的民俗地势,近些年来渐渐变得越发离奇:赤目的山猿出没,百足之虫缠身的僧人,迷雾笼罩的村落,其中"不死"二字被频频提及。
联想到药师永真提及过的"修罗"一事,让宗马不禁生出这样的念头:
莫非,那些传言并非只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吗?
他那样不经意间浮现出的认真思考的神情,全部被身边的义典看在眼里。
已是入夜,永真整顿一下衣裳,解下白天高高拢起的发髻,正欲就寝前听到套廊下传出脚步轻声。
武者的感官异常灵敏,即便是隔着一层纸门,光是经由脚步声的轻重缓急就能辨识出来人的身高体重。通过如此轻捷的步伐声响,药师当下就得知了门外之人的身份,因此在推开纸门迎接的时候并没有显露出意外的神色。
“宗次郎并不知道我来这里,不过大概很快就会追来就是了。”
披着一袭灰衣的佐藤义典背朝着女人半开的纸门,用不大的声音说。他盘腿坐在套廊下,从身后只能看到他头顶上高高的发辫。
“大人深夜登门来访,可是伤口疼痛需要处理?”
关于来客心中用意,永真早已洞悉透彻,表面上却明知故问。
“有件事,我想向药师大人打听一下。”
“大人但讲无妨。”
“宗次郎在这之前是不是向大人您询问过关于‘不死’一事?”
“此话怎讲?”
“直觉。”
药师将额头抵在门框上,默默地微笑起来。对于义典色彩鲜明的回答,她感到既是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
“是的。久岛大人他在晚宴后曾经找到我,打听过流传于苇名各地的‘不死’的传言。”
隔着纸门的缝隙,永真看见那个夜色中的背影垂下了双肩,继续道:
“佐藤大人可曾听说过‘龙胤’?”
“是指龙的后嗣吗?第一次听说。”
“正是,在这苇名国曾有婴儿在降生之初就受到祝福,因而流淌着具有起死回生的力量的龙之血脉。通过缔结不死的契约,身怀龙胤的御子能够将这种力量分予契约者,使其成为龙的眷族。”
“吾师道玄曾通过收集源之水发现具备相似能力的‘变若水’,但终究是劣化的回生之力,服用过后只会让人丧失理性。同门的师兄道顺曾致力该研究,不过自从半年前矿山的大火之后,就已经消声觅迹了许久。”
永真的声音将整件事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无从听出悲喜好恶,只是诚实又温厚地向门外的异乡人讲述着发源于这片芦苇之地的神怪异话。
“那也是弦一郎大人所求之物,为了挽救日渐衰败的苇名国。”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药师的语气悄然间变得有些微妙。
“宗次郎也知道这些吗?”
“不,上述这番皆是不可为外人所知的秘话。但以久岛大人的洞察力与行动力,也许已经获知全貌也说不定。”
“既然是密话,为什么又要向我透露?”
义典侧过头问道。
“只当是同士之间的悄悄话罢了。”
药师巧妙的回答让他当即悟出其中意味,白净脸庞上转而露出苦笑。
“'同士'是吗?如此说来,永真大人也为我很好地保守住了秘密呢。”
"不敢当。”
“...实在是不胜感谢。”
说完,佐藤义典转过身来,向着女人身前的纸门叩首而跪,整齐的发辫像缎子一样柔顺地向前面滑落下来。
细细看来,这人不仅皮肤净白,整张面孔上都透露出妇人之相。这样的事并不稀罕,四国的长曾我部元亲,占据“两兵卫”半壁的竹中重治,信长身边的知名武将森兰丸皆是如此。不如说男子女相是这个时期相当常见的事,这也或许是义典没有受到过多的质疑的原因。
“听说大人少时曾研修汉学,不知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佳句。”
佐藤义典即将离去的那一刻,药师抛出了意味深长的话语:
“‘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
“白乐天的诗,略有耳闻。”
“正是,近日空暇之余翻阅了些汉诗,自觉这是非常凄美的一句。等到来日,大人若不嫌弃,还望予以答惑。”
“随时欢迎,永真大人不必客气。”
相互表达谢意后,少顷,来客显得有些匆忙的脚步声渐渐走远,灰色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之中。
“...在这样的心情上,我们也算是同士吧。”
语毕,烛火轻熄,连同女人眼底闪烁的残火一同黯淡了下去。
“这是不寻常的事。”
说话的是一位端坐在宽绰谒见室正前方的男性,身着用金线绣着梅纹的葱心绿大氅,光光的头顶梳着月代。虽然语气听上去尚且年富力强,但观其面庞已经可见老境。
“卿不愿做已经元服的义章的傅役,却执意想要辅佐景千代?”
“正是。”
底下跪坐的一名青年将额头贴在地板上,受如此大礼者,想必不是一般人。
“在下斗胆向氏章大人做此谏言,请允许在下成为二公子景千代的监护人。”
佐藤氏章眯起眼睛,目光中却透露出机敏:
“原因为何?”
“义章大人自幼勇敢刚强,有武人之风,但若只是逞一时之勇,则未来难挑家业大梁,因此需一位善谋者助其一臂之力,此事非在下所能及。景千代大人心思缜密但不善武力,在下唯有剑术可倾囊相助。主从之间相互完善,互补短板,佐藤家才可得以长久。”
“卿仅是在公馆见过景千代几面,就作出这等判断?”
“昔日在下曾在宅邸处与景千代大人对弈过几局。‘通过棋局洞悉弈者性情,以小见大’,此乃大人您过去的教诲。”
青年的回答无形间反手将了老家督一军。
“这般执着于景千代,卿可知老夫言外之意为何?”
在此处,氏章略施小计,倘若青年回答“知”,便做实他居心不良;若为“不知”,则谴责他这等冰雪聪明的人怎会看不出端倪,定然是在假装。无论如何,他都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试图让这样难得的才华横溢的家伙留在长子身边收为家臣。
听罢,青年没有着急做出回答,而是从怀中取出一块白布与一把短胁差,在老氏章惊诧的视线中果断地将短刀刺向自己的面颊,沿着嘴角以上划开一字型的一道伤痕。手指蘸着从那伤口中涌出的汩汩热血,在白布上以血为墨一笔一画地写下了郑重的誓约书:
「久岛宗次郎宗马,以毕生之性命起誓,全心全意扶助佐藤景千代大人并护其周全。赤胆忠心,神佛可鉴。」
伴随着血沿着下颌滴落在地板上的轻响,宗马写下结尾:
「矢志不渝。」
画下花押后,他双手将这份誓约书奉与老氏章。如此行径使得老家督心中倍受触动,将这封用血写下的誓言书捧在手中一遍又一遍地默读着。
青年等待着老家督的答复,一声不吭地保持着那样跪拜的姿势,创口的血安静地流到地面和衣袖上,逐渐凝结干涸起来。
良久,老家督不慌不忙地将誓约书折叠整齐,放进一旁的锦盒里,用一种与方才截然不同的音量开口道:
“若是卿执意如此,就请卿辅佐其至于成立。”
“定当万死不辞。”
“...景千代之事就拜托卿了。”
不知是谁,想到了尚在久春时发生的,如此久远的事。
“大人!您这是作何用意?已是夤夜,还请您早些就寝。”
上上下下将天守阁搜了个遍,久岛宗马终于在空无一人的道场找到了深夜乱逛的少主人。此时义典正用牙齿咬住布条将木刀的刀柄绑在右手上,见此情形的宗马慌忙快步上前似要阻拦,义典却粗暴地往旁边躲闪着,像是赌气耍横。
“取一把木刀来。”
青年不做应答,只是忧心忡忡地站在原地注视着义典的动作。
“拿木刀来,宗次郎。”
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义典抬起眼睛,目光掠过青年手中的一只葫芦,费劲力气系在刀柄和手掌上的结扣看上去疙疙瘩瘩很是简陋。
“还请您说明用意。”
“久违的剑术练习而已。”
“若是真心想要练习的话,大人大可等到明日。您的伤势刚刚痊愈,今夜就暂且歇息,明日在下定当奉陪。”
正是这样沉着的应对让义典的眉头抽动了一下,像是被激怒了一样,他抬起手上的木刀,架在与他相对而立的青年颈侧,冷言冷语道:
“如果现在架在你脖子上的是真刀的话,你就已经因为违抗主上的命令,人头落地了。”
“在下的生命已在多年前交付于您。倘若大人此时此刻要取在下性命,在下也甘愿为您将其奉上。”
“你——!”
木刀高高扬起,气急败坏的义典咬牙切齿地将其全力向着宗马的脖颈挥下。
随着“咕咚”的声响和视野中一阵天旋地转的晕眩感,高个武士的身躯以一种仰面朝天的姿势整个人被撞倒在地板上。
除了背部的撞击和胸口的沉闷感以外,颈侧并没有传来被击打的疼痛。
地板很冷,简直比窗隙间投射进来的银色月光还要清冷。朦胧光线下,空气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的颗粒飞扬起来又缓缓落下,不知道那究竟是雪粒还是灰尘。
即使是在被仰面撞倒的情况下,青年在最后一刻都保持着一种将冲击最小化的姿态,用紧贴胸口的怀抱保护着少主人的身躯,不叫那二次愈合的伤口再次崩开。
那只葫芦在他选择伸手抱住义典的时候被毫不犹豫地抛向了身后,从葫芦口咕嘟咕嘟地流出的东西在地板上漫开一片晶亮的痕迹。
“那也是为了我吗?”
感觉胸口处环抱的身躯蠕动着,那把木刀抵在他的咽喉处,宗马慢慢地睁开眼睛。
他并不是第一次如此靠近义典的面庞,却一时之间陷入了一种魂不守舍的状态,心房因此怦动震颤着。
久岛宗马此人平生少有地产生了畏惧之心。
他对这种白丁武士一样不成熟的感情既愧疚又痛苦,并极力压制着不让它溃决。
“若是为了我,就承受那样的东西...”
与那朝夕相处,再熟悉不过的声音一同传来的是脸颊上温热的触觉。一滴一滴,落在面颊那道深红色的伤疤上。
“...那我宁愿死在那天夜里。”
(只狼paro言情)残之春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宫墙:三废为王
- 简介:世人只见到嫁入帝皇家的风光,谁能想到这华美的宫装背后,藏着多少红颜泪。本小说来自宫廷手游《熹妃传》。
- 24.3万字2年前
- 燕惊鸿
- 简介:桑颜,一个前世家破人亡的世家千金。重生归来,她不再躲藏在深闺大院中,掌控全局,报仇雪恨。哪知,那传闻中的病秧子世子却对她一见钟情,开始不停的骚扰她。“病秧子”世子:阿颜,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病秧子”世子:阿颜,别走。“病秧子”世子:阿颜,你的手帕还与你。桑颜到最后发现,自己好像沉沦进他的温柔乡了?!
- 0.2万字1年前
- 徒儿又犯错了
- 简介:苏河辰怎么也想不到,下山捡来的“土包子”竟然是个可爱的少女,还迷恋上了她。
- 0.7万字1年前
- 哥宝废后
- 简介:她还有七个哥哥.她还有皇后之位.她还有她在襁褓中的孩子.有她的夫君.你说她怎么舍得在近水楼割腕自杀?
- 0.4万字1年前
- 晨文随笔
- 简介:此书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作者脑袋发热时想到的一些东西写成的。里面可能有奇幻灵异故事、动人爱情故事、美味爱心鸡汤……类容丰富,只有你想不到
- 0.3万字1年前
- 宫乱:权位之争
- 简介:不喜勿喷
- 1.7万字10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