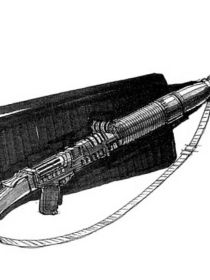第八章 书法
雪这种东西,远看着是那么回事,可碰到太阳一晒,消融成水再仔细看,就是污浊不堪了。
年后已到二月,冬过去了,春即将要来,天气也愈发暖和起来,日头只消一照,不过一层薄薄的雪很快就化了。
大兄说我是通透之人,只需好好养养自己的性子,以后自当前途无量,我不晓得他哪里来的自信,只觉得被他推拉着往前走,再不似从前那般安逸放纵了。
“张迁碑?”
我所执的书卷被人抽出手,未干的墨迹略为古朴,正摹到“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那段,被人朗朗地读出来,闹得我很是脸热。
大兄手里的纸张自桌上铺平,俯身笑眯眯看我:“难得你喜爱这端持的张字,此隶虽说不难,却也有些变化,你年纪轻轻就能悟得其中五六分,已经算是大才了。”
能被挑剔的大兄如此鼓励,实在令人感动。
近来的努力总不算得白费,我的心肝激动地砰砰直跳,接过他笑眯眯递来的纸,平日拿刀枪的手紧张地发着颤:“还好,还好。”
哪比得上他的万一呢,我不过是追随着他的脚步笨拙地模仿罢了,若非有他的鼓励,凭我的性情哪能走到今日。
上方的人舒朗一笑,自我身旁坐了下来。
他啧吧着嘴,捉起我的手煞有介事地端详起来:“我们阿劼可是大英雄大将军,上阵杀敌从不手软,怎的碰到写字这事就如此害羞了?”
这问题问的,我怎么知道!
我受不了他的调侃抽出了手,凭借着自己的急智转了话题:“您只晓得我爱张迁碑,但您定然不晓得我为何喜欢这字。”
“哦?”
他好奇地看了眼我,面上正经了三分:“愿洗耳恭听。”
“於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求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我抚着纸张念罢,深深地看向近来愈发清简的郎君:“若天下的官吏皆是这样的品性就好了。”
我没有他懂得那么多,可这夸人的话我喜欢,这字我也喜欢。
其实这是我幼时与大兄的比方,可惜他当年便很有成就了,现在又身处皇帝的高位,福泽的也是天下万民,论能力和手段,也绝非区区一届县令可比。
大兄不晓得我的想法,只玉人般地凝神须臾,净爽的袖沿忽然擦过我的颊,他起身悠然负手。
阿兄幽幽地看过我,再望向远方的白云,道:“你说得不错,看来是听进去了些我教导你的话。”
“关中将旱,”那修长的指尖摩挲着袖口,对天叹了口气:“连年雪薄,关中土瘠,若再不往东迁移民众,以后可就有麻烦了。”
有麻烦……
我心头一紧,见大兄的脸上现出了几分忧色。
阿兄这人向来细腻周到,总是先人一步地预料到危机,以我从小的经验来看,他所烦恼的事九成九都会发生。
这可怎么办哪。
我脑袋转了一圈大约想到关窍,十二分坚定地握住他的手:“无论兄做什么我都支持您,您要我干什么我便干什么。”
我虽然不大懂治政,但我相信他。
“我的阿弟总是这么地……”
他回过神来,与我亲昵一笑:“乖巧。”
那漂亮的眼睛里,是满心满眼的信赖。
谁说他是个端庄持重的人呢?
大兄不做什么皇太子了,昔日压抑的那些性情于是放纵了些,而今太和元年,继幼童之后我再次看到他写意的一面。
我总以为大兄身上有一种狡猾的气质,就如他的话,每句都是仁义道德礼智信,每句却各有关窍。又如王献之的字,初看轻松快意、骏利放逸,细瞧别有一番妩媚秀丽,灵动臻妙的气韵。
他是顶顶的聪明纯澈之人,而我只是世间芸芸众生而已,我与他相形见绌,却犹敬非常。
不过再是灵动,阿兄对我却总是十成十地真心,几乎是习惯性的信任,从来没有猜忌过我。
我豺狼的本性收了七分,淡定地理了理自己微生褶皱的袖:“那是,我可是一直很乖的。”
多少有些幼稚了。
阿兄却唯独喜欢我的幼稚,还是幼时一般地安然揽过我,自廊苑里安安静静地晒了会儿太阳,直到嫂娘到来。
嫂娘正怀着身孕,据大兄估摸着已是七月了,此时溜达到了这处,显然不是来晒太阳的。
我冲着那衣着朴素的娘子憨憨一笑,挣出了阿兄怀里:“嫂娘好。”
也不晓得为何,我这嫂娘虽贵为皇后,却总是将自己打扮得很是素净,她初与阿兄成婚是什么样,入宫里当皇妃便是什么样,这些年来不争不抢温温和和的,不见变化多少。
我很有眼色地搀着她坐下,他俩凑成一对儿坐在上座,不见半分皇帝皇后的威严,还是如常相视一笑,瞧得人愈发紧张。
阿兄和阿嫂终究是同类人,只是阿嫂为人更为端持老成些,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只消淡淡看我一眼,便能轻易分辨出我的心思。
而我总是害怕在她面前出丑,是以在她面前一向很矜持。
普天之下女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嫂娘,一类是别的女人,此妇成婚的时候我就不敢招惹,更莫说是现在了。
当然我的生母属于道行高深的那类,不说也罢。
她惯常宽和地看过我,斟酌着看向阿兄:“我看着阿劼像是长大了。”
李建成x李元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碧蓝中的现代战舰
- 简介:当一个现代战舰肝帝来到了碧蓝航线,现代战舰又回和二战科技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手机没了,只能周六周日更了)
- 8.1万字2年前
- 少年特种兵学校cp
- 简介:封面瞎填的
- 0.3万字2年前
- 高塔中的盛夏
- 简介:民国十六年,战事混乱,列强纵横,四处横尸遍野,芒城成为了这场纷争的主战场。
- 1.0万字1年前
- 特种兵学校CP(星际战士版)
- 1.6万字11个月前
- 魂飞大唐
- 简介:历史,穿越
- 1.3万字1年前
- 中央星系:机动特遣队
- 简介:这不是地球,却有与之相似的文明;这里的科技高度发达,却与魔法并存;所有在地球上的"科幻"在这里似乎都能变为现实。在这里,有一支小队,正借着夜色的掩护,奔赴下一个目标……(本人高中牲一枚,毫无写作经验,还请诸位轻点骂~)
- 1.2万字1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