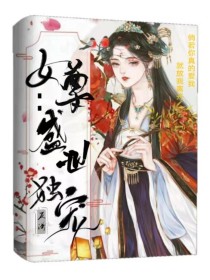序章【04】
第二天的午时,苏雪衣早早就在三楼雅间里坐着了。
一同在雅间内的还有姜明和胡继生,两个玉面玄袍的少年人坐在一起原本很是养眼,可惜其中一个根本坐不住,像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绕着桌子乱转。苏雪衣被他晃得眼晕,无奈地开口:“我的祖宗,你倒是消停会儿吧!”
姜明闻言顿了脚步,那股停不下来的劲却好像从脚转移到了嘴,开始念叨个不停:“他会不会不来?万一不来,我们岂不是白费力气?”
苏雪衣道:“那人是位读圣贤书的君子,不会言而无信。”
虽说苏雪衣已经许多年没用过魅惑这种小计俩,但九尾狐族的看家本领还是刻在骨子里,没让她给忘个一干二净。美人相邀,又有魅术加持,苏雪衣不信他不来。
姜明又说:“要是他来了却不肯向我们交代怎么办?他真是我们要找的人吗,文昌侯可不止一个儿子……”
苏雪衣:“……”
她忍无可忍,干脆走出了里间,眼不见为净。
说书人朗朗的声音又从楼下传来,苏雪衣听了一阵子,很快失了兴趣——说的是当今皇帝的生平,有年幼时的经历,也有现在的丰功伟绩。她和这位帝王还算得上是熟人,说书人能念出来的故事,和她了解的东西也是八九不离十。
虽然苏雪衣不是主角,作为曾经大名鼎鼎的妖后,还是在过程中被提及到了。也不知道是谁起了个头,人们纷纷议论起当今圣上不肯选皇后的事情来——据说前两日上朝的时候有大臣提到此事,要求填补后位,年轻的帝王勃然大怒,降了他两级官品。
苏雪衣无奈地想,虽然小皇帝现在行事雷厉风行了许多,但唯独叛逆这一点还是没变。别人要他做什么,他偏不做什么。前世要是没有她护着,这样的性格,在皇室里不知道要吃多少亏。
正这样想着,楼梯口忽然探出个人来,正是张珏本人,身边还带了个小厮。苏雪衣娴熟地露出一个职业微笑,做出“请”的手势:“恭候公子多时了。”
张珏犹豫了一会,到底还是走了进去,大概是没想到雅间里还有人,看见胡继生和姜明时愣了一下。苏雪衣见缝插针地把门一关,将人堵死在屋子里,还是一副职业假笑:“昨日请公子来,实在唐突,但也是无奈之举,还请见谅。”
小厮被这严刑逼供般的架势吓了一跳,两个少年则面面相觑——说是见谅,她可没有半点歉意的样子。
张珏叹了口气:“你们是来问彩蝶的事情吧。我知道,这件事迟早是要有人来问的。”
彩蝶就是那个在命案中死去的丫鬟。
胡继生从怀里掏出一个令牌,给他们两个人看了一眼,还没等苏雪衣看清便立马收了回去,又连忙制止了两个要行礼的人,问道:“二位不必如此,我们也只是跑腿的。张公子可否详细说说?”
苏雪衣挑了挑眉——感情他们还是不信任她,誓要把自己家主子的身份保密到底了。
“……”张珏沉默了一阵,慢慢道,“她是我的贴身侍女,侍奉我也有十年八年的了。”
这位文昌侯府的小侯爷还真是个书生,自小励志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十年八年里两个人一直相安无事,彩蝶也尽心尽力地当着侍女的角色。然而科举两次未中,意志消沉的张珏失去了信心,开始流连烟花之地。直到一个多月前,东窗事发,文昌侯勃然大怒,关了他的禁闭。张珏在屋内借酒消愁,一醉之下,同自己的贴身侍女彩蝶发生了关系。再之后没多久,彩蝶便香消玉殒。
苏雪衣听完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问两个少年道:“你们认为这故事怎么样?”
姜明中肯地评价了四个字:“哈哈哈哈。”
于是苏雪衣又转向张珏:“他觉得你在说笑话,你说怎么办?”
张珏:“……”
胡继生思索了一下,将姜明那四个字翻译成了比较能让人听懂的人话:“漏洞百出。”
其一,流云巷不是普通的乐坊,即便是洇华之内的官宦人家,也没有人敢把它当成寻常“烟花之地”来看待,如果张珏只是在流云巷里看了几场歌舞,断然不至于让他的亲爹大发雷霆。其二,即便被关了紧闭,张珏这种自小就泡在书堆里、甚至去流云巷看姑娘跳舞都滴酒不沾的书呆子,怎么会因为被关禁闭太无聊而借酒消愁?
再说就算借酒消愁,这书呆子也不像是个喝了酒就会跟自己的侍女上床的角色,这理由虽说合理,却实在有点牵强。
然而这些问题,张珏给出的回答都是:不记得。
“我前段时间得了病,许多事情都记不清了。”张珏说,“这些事情也一样,而且还是身边的人告诉我的。”
苏雪衣满脸写着不信。
姜明思忖了半晌,问道:“彩蝶姑娘的尸身,您看过了吗?”
“没有。听说她死得很惨,死前还在惨叫呼救。”张珏说,“家里的人都说,她临死时手里还握着样东西,攥得死死的。”
苏雪衣心中一动:“是什么?”
张珏道:“一只发簪。”
苏雪衣微微眯眼。
胡继生追问道:“什么样的发簪?”
“抱歉,我并不知道。”张珏摇了摇头,神色颇有些黯然,“我同她有多年相处之情,虽然犯下过错,但也想过对此负责,却没想到……”
他今日穿的是一身白衣,与昨日流云巷中那一身略显华贵的装扮截然相反,领口的毛边裁得干净整洁,真有一副谦谦公子温润如玉的模样。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怎么也不像是会因为科举不顺而纵情声色的人。
苏雪衣突然问道:“公子为何流连于流云巷?”
张珏茫然地看了她一会儿,像是没有明白她在问什么。苏雪衣正要再问一次,却听见他说:“我不记得了。有什么原因让我一定要去,可是我不记得了……”
他痛苦地捂住了脑袋。
小厮扶起他,对他们道:“彩蝶去世后,少爷就大病了一场,高烧烧糊涂了,脑袋一直不太好……今日他说得已经够多了,请各位大人放过他吧。”
张珏休憩了片刻,似乎从头痛中缓过神来,又忽然想起什么,从袖袋中取出一只发钗放在桌上,对苏雪衣说:“姑娘昨日的东西落在我这了。”
这对话颇有些耳熟,两个少年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想——她好像真的很喜欢随手把自己身上的东西送给别人。
交谈结束以后,胡继生客客气气地把人送了出去。姜明像没脊梁骨的章鱼似的瘫在椅子上,略带郁闷地说道:“这都是什么事?一件比一件离谱,明明一听就全是毛病,可就是想不明白缘由。”
苏雪衣抱臂倚在房梁边,一只手还把玩着那只被还回来的白玉钗。她没戴帷帽,瀑布似的长发极为随意地挽了一半,发间唯一的一根簪子是和衣服相同的白色,款式像只削尖了的长筷子,敷衍得简直让人觉得若不是有十二分的必要,她大概随时都会披头散发地上街。
并且姜明再一次注意到,一双嫩白的足遮掩在层层叠叠的纱裙下,看得不清晰,但确实——没有穿鞋。
如今人界的风气虽然已经开放了不少,但如此放荡不羁的,到底还是少有。姜明只看了一眼,想起师兄那一巴掌和训斥,连忙红着脸移开了目光,识趣地没有问。
苏雪衣丝毫没注意到他的异样,羊脂白色的玉钗在指尖灵活地翻来转去,丝毫不担心它会掉下去摔坏似的。“那个小厮有问题,你看出来了吗?”
姜明细细一回想,似乎确有其事:“说起来,他好像一直在……看你?”
苏雪衣眯起眼笑了一声,勾起的嘴角带了点玩味的嘲讽。
有一瞬间,坐在对面的少年突然觉得她不像是个乐坊里的女子,但究竟该像个什么样的人,一时半会又说不清楚。
她说:“我有件事情需要你们帮忙。”
刚送走张大公子回来的胡继生从门口探进个头,问道:“什么事?”
苏雪衣:“挖坟。”
二人:“……”
二人:“啊?!”
-----------
苏雪衣的直觉从不出错。当天晚上,张珏身边的那名小厮便将今日醉仙阁里的见闻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别人。坐在主位上的贵妇人神色阴郁地听完了汇报,沉着脸问:“你说的可属实?珏儿昨日当真去见了她?”
小厮道:“小人不会认错。”
贵妇人沉默了半晌,缓缓道:“她若真是国师身边的人,这事就复杂了。”
还未等她权衡出一个所以然来,便有人推门进来,向她请示:“夫人,有位姑娘在侯府外求见您,说自己叫九娘。”
贵妇人神情一冷,道:“就说我不认识什么八姑娘九姑娘的,赶出去。”
下人点头称是,不料还没转身出门,一个清清脆脆的笑音便自窗外传来,说道:“怎么,夫人这么不愿见我?”
屋内的人皆大惊失色。却见一阵风吹过,镂空的雕花窗忽然打开,一袭白衣的女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翻进了窗户里,翘着二郎腿坐在窗栏上。明明是极其不雅观的坐姿,却硬生生让她坐出了一种潇洒肆意的漂亮,像只脱胎于山野的山妖精魅。
贵妇人面如菜色,尖叫一声:“来人!”
“夫人别着急,这屋子周围被我下了结界,里面的声音一时半会可能传不出去。”苏雪衣掸了掸袖子上并不存在的灰,从窗户边上跳下来,“夫人不打算请我坐下吗?”
她嘴上像是在询问,然而身体却完全不给面子,挑了张看起来顺眼的椅子,转身一屁股就坐了上去。贵妇人气得发抖,指着她怒骂:“放肆!你这妖女是怎么进来的?”
苏雪衣笑眯眯地说:“夫人都说我是妖女了,您说我是怎么进来的?”
她的手肘搁在桌子上,撑着下颚,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话锋却陡然一转,笑意冷了下去:“不过如今两界已经签下协议,和平共处,互相尊重,这可是圣上下的旨意。夫人骂我是妖女,算不算是……抗旨呢?”
如今虽然两界合并,但毕竟共处时间仅过了十二年,朝中仍然有某些顽固派仇视灵族,天天想着在这件事上如何给皇帝下绊子。苏雪衣找胡继生二人补过功课,朝中文昌侯虽然态度中立,但其姻亲武安侯袁家却是典型的仇灵派。不仅如此,袁家的势力遍布朝野,其嫡次女嫁给了文昌侯,嫡长女则入了宫,如今位列四妃之首,更掌管着宫中凤印,以至于朝中明里暗里仇灵派的人数依然不少。
帝王最恨这一派。
袁夫人的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不知是气得不会说话了还是自知理亏,只是恶狠狠地瞪着苏雪衣,好一会儿才道:“来人,给九姑娘上茶!”
苏雪衣懒洋洋地道:“茶就不必了,我心胸狭隘,就怕夫人会在茶里放些什么东西。我今日来是因为贵府的下人昨天一直盯着我看,我就觉得奇怪,是因为贵府曾经与我有过什么过节,还是因为是我美貌太过,让人移不开眼?所以特地来问问。”
说罢,还往那小厮身上一瞥,丢了一串带电的秋波。
袁夫人大概是生平从未见过如此不知礼数还恬不知耻的女子,整个人都气成了一只河豚,却又明白眼前这看起来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子不是盏省油的灯,更忌惮苏雪衣身后的那位角色,不敢多说什么。
……尽管实际上,苏雪衣只是在狐假虎威,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胡继生和姜明口中那位“大人”到底是谁。
好半天,袁夫人才压下了一点火气,没好气地道:“九姑娘今天来,究竟有何贵干?”
“两位小道长今日没空,我家大人还未归京,所以只好让我来问问。”苏雪衣道,“我听闻贵府上个月死了个名叫彩蝶的侍女,死时手里还握着只发簪?”
袁夫人心中一沉,面上却还不动声色:“确有此事。”
她心中已经打定主意,如果对方问起那发簪的模样,就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见过。不料苏雪衣却完全不按常理来,她依然一手托着自己的下巴极其不正经地坐在椅子上,另一只手捻起一件物什,晃了一晃:“那发簪,是长这样吗?”
那是只做工精致的簪子,用玉石雕成一朵半开的桃花,花蕊是一块蓝色的宝石,通透澄澈,触手生温,在灯光下散发着淡蓝色的光华。
袁夫人差点昏过去。
她离得远,发簪的体积又小,看不真切,若是离近了看,必定会发现端倪——这是个惟妙惟肖的高仿品。苏雪衣让姜明二人去开彩蝶的棺只是为了确认,其实她心里早就知道,那只发簪八成不会是彩蝶的。
关于彩蝶死后这东西的去向,本来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苏雪衣好巧不巧地遇上了身上带着灵力的红药。于是她瞎猜了一把,在洇华各种各样的首饰铺里找了一天,终于买到了一件款式差不多的,用来以假乱真。如今看来,这只发簪,如今大概是戴在红药的头上了。
“我观这小玩意气息不祥,像是有魔气在内。”苏雪衣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指关节敲着桌子,说道,“夫人最好还是如实禀报,否则待我家大人查到了什么,武安侯府恐怕……”
她意味深长地住了口,威胁之意毫不掩饰。
“……”袁夫人咬牙切齿了半天,终于还是开了口,“两个月前宫中有宫女暴毙之事,想必九姑娘也已经查过了。”
苏雪衣笑而不语,权当默认。
“宫中之事本不该由我这妇道人家置喙,但两月前我得了陛下应允进宫探望贵妃娘娘,她对我说起宫中下人偷盗首饰,倒卖出宫的事情。”袁夫人说,“这遭过盗窃的宫殿里也包括了棠梨轩,那宫女生前受过陛下恩惠,死了以后许多首饰却不翼而飞,一查才知道是被变卖出去的。可是不查还好,查了却发现后宫牵连甚广,若要彻查,定然会影响宫中势力的平衡……贵妃娘娘为此事殚精竭虑,连觉都睡不好。”
苏雪衣拉长了调子“哦”了一声:“所以为了不伤和气拉仇恨,贵妃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把这件事糊弄过去。”
难怪棠梨轩里连宫女手上的镯子成色都这么好,原来买镯子的钱是从这里来的。
袁夫人没顾得上恼她阴阳怪气的腔调,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那发簪就是从棠梨轩中流出来的,险些就别卖到宫外。我……我也是一时迷了心窍,觉得这蓝宝石十分好看,所以才……拿回来以后也是一直锁在柜中,从未使用过,谁知有一天不知怎么不见了,却没想过是被那丫头偷走了!但是魔气我却是闻所未闻,我只是个普通妇人,怎么可能认识什么魔气?”
“你可知道,宫里的玩意多半是陛下赏的,”苏雪衣瞥了她一眼,“偷盗御赐之物,该当什么罪来着?”
袁夫人脸色惨白,一副想要吃人的模样,忍了半日,愣是咬着牙道:“我自知罪孽深重,但魔气一事,我敢以性命担保,袁家与张家上下绝不知情,还请大人明鉴!”
苏雪衣暗觉好笑——最开始时叫她妖女,后来叫她一声九姑娘,现在倒好,直接叫大人了。翻脸快如翻书,川剧变脸演员都要自惭形秽。
“夫人据实相告,我怎能有不信之理?”她慢悠悠地起了身,脸上似笑非笑的,叫人压根摸不准她这话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敷衍,“如此,我便回去禀报了。”
说罢还不卑不亢地行了个礼,大摇大摆往门口走。走到一半,突然又回过头来,像是刚刚想起一样说道:“对了。”
袁夫人刚松了一口气,冷不防被她这么一吓,那口气登时郁结在喉咙里,不上不下地呛了个半死。苏雪衣笑吟吟地继续气人:“其实我根本没下屏障,这屋子里的人说了什么,外头全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夫人可要小心,府里若是有什么心怀不轨的人听了刚才那番话,对您可就不利了。”
袁夫人:“……”
待苏雪衣终于离侯府的门远远的了,她举起一个杯子,狠狠摔在了地上,仿佛摔的不是个杯子,而是张笑吟吟还贱兮兮的美人脸。
小厮吓得当场跪下:“夫人息怒!”
袁夫人却没有第一时间宣泄她的火气,只是阴沉沉地坐在主位上,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她的胸口起伏了半晌,终于将满腔怒火平息了一半,才哑着嗓子慢慢开口:“你下去吧,顺便清理一下屋子周边,看看有没有人听见了什么不该听见的。”
又有人推门进来,小声向她报告了些什么。袁夫人听完脸色一变,腾地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你说什么,那东西真的不见了?!”
一滴冷汗当即从额角流了下来,袁夫人的脸色苍白铁青,比方才见苏雪衣还要难看几倍。她在原地来回转了几圈,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说道:“这个人,不能留。”
小厮神色一紧。
“如今国师尚不在京,我还能与她周旋。但若是等国师回来了……”袁夫人越想越是胆战心惊,几乎控制不住自己颤抖的手,“一定要趁她与国师通信之前,解决掉这件事。”
灵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绝世宠妃樱辞著
- 简介:他握住她的手腕“怎会有那么多男人来找你嗯?下次绝不允许”墨颜阙×苏沫柔
- 3.7万字2年前
- 女尊:盛世独宠
- 简介:[没完结,但最近在做大整改。]
- 13.3万字2年前
- 玉儿
- 1.3万字1年前
- 杳霭流玉:丞相夫人不简单
- 简介:【签约日期:2023年1月27日】镇国将军花臣,年少时意气风发,即便步入中年也一心为国,最后却落得被灭满门的下场。皇帝唯一的善心,便是留了他的五位孩子。三女儿花芷年仅五岁,被国公爷一家收养,改名徐宛宁。一场大病,忘却一切,所有人都以为她真的不记得了,可事实是如此吗?团团迷雾,身世之迷,以及花芷的真正实力……【甜宠文,复仇,女主马甲多,喜欢记得点个收藏呀!】
- 2.3万字1年前
- 刺客伍六七:人生
- 简介:柒的父亲不是莫浪,但姓莫
- 0.1万字1年前
- 重生女配之攻略
- 简介:她是一部小说的女配,遭男女主的陷害,自爆落个死无全尸;一个被天道所追杀的神秘男子帮助下重生,交易,最后谁陷入,谁轮陷……
- 0.5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