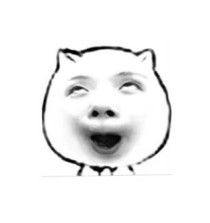第十八章:你我就差一点距离
我越来越偏爱做两件事。
一件是喝酒。
我的酒量越来越好,啤酒、白酒、清酒、洋酒,只要是酒,我通通能像喝水一样一饮而尽,它们的结局也跟水一样,短暂地停留在我的身体中之后义无反顾地奔向洗手间。
另外一件事就是顺着阳光,举起剪刀,对着所有分叉了的头发毫不留情地“咔嚓”一声,剪掉。
看着那一地的分叉,我很想问问你,是不是头发长长了就一定会分叉,就像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一定会分开?
冰箱里已经空了,唯一剩下一盒雅士的酸奶也已经过期,最重要的是,我没有酒了。
我不得不沮丧地打起精神换套衣服戴上墨镜涂上防晒霜出门采购食物,一直以来你都欣赏我的生活态度,无论在家里多么随意邋遢,出门一定要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紫外线最强烈的中午,滴水未进的我感觉自己随时有可能晕倒在柏油马路上,过往的车辆和行人都这么多,这是个喧嚣热闹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一切都那么容易失去,食物,工作,住所,幸好我还有爱情。
在一切未知的变动中,我有对你的爱情,这足够我在漫长永夜里慰藉自己寂寞的灵魂。
我推着推车在偌大的超市里闲逛,像一只即将冬眠的野兽给自己贮备食物,以前为了保持身材而刻意拒绝的膨化食品,可是现在,不必了。
你曾经半真半假地说我最大的优点是自律,最大的缺点是太过自律,我知道你另有所指,于是含笑不语。
月球围绕地球转动,地球围绕太阳转动,这是必须遵循的轨迹,如果缺少自律,后果堪虞。
一边想着这些往事片段,一边走到了酒柜面前,连我自己都没有察觉,看到这些各色各样的瓶子整齐地陈列在我眼前时,我原本麻木的面孔竟然绽露了笑容。
在收银台结账的时候,我前面的女生刚好缺一块钱的零钱,算我多事,好心帮她付了。
她转过身来对我说谢谢,干净的面孔,澄净的眼神,由衷的语气。
藏匿在墨镜后面的我,微微怔了怔,然后挑一挑嘴角:“不客气。”
我绝对不会认错,曾经你的手机壁纸就是她的照片,她是林思思,跟我爱着同一个人的林思思。
王宇哲,我不曾料想,在你远离我们的生命之后,我竟然会在这样的场合看见她,如果她站在我的背后,是否能清晰地发现,我就是曾经安放在你钱包里的那张黑白照片上的背影。
真心话大冒险真不是个好东西。
第一次见你,就因为这个游戏给你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印象。
我穿着一字领的黑色雪纺,上面有点点小碎花,露出嶙峋的锁骨,绷紧的铅笔裤,女人味十足的着装却不伦不类配了一双帆布鞋。浓墨重彩的妆容已经掉了一半,不用照镜子我都能想象黑色眼影跟睫毛膏被汗水晕开之后那张面孔有多狰狞。
本来是一群朋友的聚会,中途小卉说有新人要加入,是她玩游戏认识的朋友,很英俊的男孩子。
所有的女生都欢呼雀跃,只有我没当回事,英俊的男生太多了,哪能个个都关注。
可是偏偏那么巧,我打开包厢门,你就站在门口彬彬有礼地看着我,我仰起通红的面孔对你笑:“帅哥,找小姐啊?”
多么狼狈的开场方式,天知道我是多不情愿接受这样的玩笑,可是比起要我认输喝酒……还是两害相交取其轻。
愿赌服输,我输了,就要玩得起:打开包厢门问你见到的第一个异性是不是要找小姐。搞清楚原因之后,你在我的身边坐下来,我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连“不好意思”四个字还只刚到嘴边,你就义正词严地对我说:“你像个什么样子。”
我笑意盈盈地看着你,一点辩解的意思都没有。
可是轮到你的时候,你也十分狡猾,选择了大冒险,一众损友提出“必须去吻今天晚上你觉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带着看戏的心情想看看这个之前道貌岸然批评我不含蓄矜持的男生怎么收场。
我死都没想到,你环视四周一眼,然后,倾过脸来轻轻地吻了我。
居然是我?
我呆若木鸡地应承了你的吻,众人哄笑过后我依然茫然不知所措,散场的时候你忽然拉住我,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你轻轻地抱了一下我,我没有挣扎也没有拒绝,而是把它当成一个礼节。
没想到你一改之前道貌岸然的样子,戏谑着同我说:“好细的腰。”
我想,那个时候,你大概是把我当成那种浪荡开放的女孩子。
但是我什么都没说,你的眼睛在夜里像寒星,真好看,你说:“美女,我送你回家吧。”我笑一笑,对你说:“不必了,美女自己打的回去。”
你真是年少轻狂,我下了的士之后才看见紧随其后的你的车,你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对我笑,那个表情的意思就是“你不让我送你我也有办法知道你住哪里。”
我看着你那副登徒子的嘴脸,不怒反笑。
你忽然又正色:“美女,我其实只想做两件很纯洁的事情,一是想打听你的名字,二是想告诉你,你的衣服跟鞋子不配。”
我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那双被人踩得看不出颜色的帆布鞋,忽然有点难受,可是我还是笑着对你说:“美女名叫苏瑾,苏瑾从来不穿高跟鞋。”
后来听说你回去之后跟小卉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中间你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第一次听说从来不穿高跟鞋的女生,太稀奇了,拜托你一定要介绍她给我认识。”
当天晚上我正要睡觉,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短信:“苏瑾,我是王宇哲。”
接触得多了,你就喜欢妄自评价我:“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子。”
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也客观地审视过自己,得出的结论是:你错了。
我一点都不奇怪,平凡如街上每一个女孩子,我上得厅堂入得厨房,人格经济都独立,学习也认真努力,我哪里奇怪?
在我某天心血来潮的时候决定要让我的狐朋狗友们都了解我居家的一面,于是一个人兴冲冲地去超市买了很多很多菜,翠绿黄瓜、深紫茄子、绿油油的莴笋、红通通的番茄,还有必不可少的青椒、红椒,再加上做甜品的黄澄澄的芒果、外表难看内心美的奇异果。
大家在客厅聊天、看电视、打牌,我挂着围裙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切辣椒的时候辣椒籽蹦到了眼睛里,眼泪哗啦哗啦流下来。
不知道谁推开了厨房的门,我眼睛里一片模糊,是谁小心翼翼地用纸巾帮我擦眼睛,是谁轻轻地揉了揉我一头乱七八糟的长发。
那个模糊的身影像变焦一样渐渐清晰起来,我从混沌之中看见你关切的样子。
有别于之前任何时刻的你,这次你的眼神不是探究,不是好色,那是实实在在的关切。
怕被你看出我的拘谨,我使劲把你往门外推,快快快,你快走。
你一边踉跄着脚步一边不解地问我:“怎么了?”我不好意思说,我每次看到你就紧张,那种掌心里会冒汗的紧张,虽然我不知道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大概知道你对于我来说跟那些男生是不同的。
有很多很多人说喜欢我,男生女生都有,我从来都是一群人里最受欢迎的那一个,所有人都觉得我可爱,只有你说我奇怪。
我做这么多事,目的都是为了向你证明我不是,类似于幼童赌气的心理。
可是我不知道,我干吗要跟你赌气?
你愿意怎么看我怎么想我怎么评价我,随你去好了,我跟你较什么劲?
胡思乱想的时候,锅里的油烧热了,我连忙把切好的黄瓜丁倒进去炒,再把在超市里买来的半成品鸡丁倒进去,撒盐,撒酱油,撒辣椒,起锅。
我做了很多很多菜,颜色和味道都那么好,每一道都是那么秀色可餐,我沉浸在对自己的崇拜中无法自拔。
最先吃鸡丁的小卉怯生生地问我:“苏瑾,这个鸡丁什么时候买的?”
我瞪着她:“当然是今天现买的呀,难道还是过年的时候留下的?”
可是众人一闻,确实有点变坏的气味了。我原本不信,结果事实让我哑口无言,气氛一时之间有点尴尬,我却不知道要如何解释这份倒霉的鸡丁责任在超市而不是我。
关键时刻,你好心为我解围,招呼大家:“继续吃。”
我勉强笑着叫大家吃别的,我去厨房看看甜品,就在我转身进了厨房的时候,我听见你的声音那么沉稳有力,他说:“这个菜吃光吧,一剩下她就要伤心的。”
我背靠着厨房门,用一句俗气的话说,心里涌过一阵暖流。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温暖的力量却让我簌簌地掉眼泪,以至于他们后来吃甜品的时候都说微微泛苦,我没敢说那是因为我的眼泪落在了里面。
很久以前我就觉得我的感情残废掉了,我应该不会再对任何一个男生言爱了,在你出现之前,不是没有人说过喜欢我,可是我看着他们的面孔,捂着自己的心口,说着同样一句话。
你是一个意外,平铺直叙的余生中一道闪电,我心里那些落满灰尘的角落在光亮之中袒露得清清楚楚。
王宇哲,我想我大概是动心了。
我们这群朋友都是群居动物,天生爱热闹,天性贪玩,所以借着你生日的机会,我们又大肆冲向钱柜。
我不知道要送你什么礼物,衣服、钱包、火机,你什么都不缺,如果干脆包个红包,又显得我苏瑾十分恶俗。
所以最后我只提了一个很大的慕斯蛋糕去,蛋糕上中规中矩地写着“生日快乐”四个字,就这样,不出错,也不出彩。
我进去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小卉她们堵车都还没有到,我把蛋糕放在桌上在你身边坐下来,安静的包厢里一时之间连空气都变得浮躁暧昧。
你轻轻握住我的手,什么话都不说。
我像第一次被你拥抱一样,用沉默许可了你的放肆。
我们沉默以对,谁也不知道能开口说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包厢的门被一群乌合之众推开,与此同时,你飞快地收回了你的手。
我心里一惊,幽幽地看向你,心里有些疑问渐渐显出端倪。
我的疑问没有持续到次日天明,在你吹生日蜡烛的时候,答案浮出水面。
一打开灯,以小卉为首的八婆们就唧唧喳喳地问你“许了什么愿望,不妨说出来娱乐一下大家”。那么多双亮晶晶的眼睛都注视着你,我心里“咯噔”一下,像是预感到你说出来的话会对我造成伤害,可是来不及,来不及,在我屏蔽自己的听觉之前,你抢先说出了残酷的真相。
你说:“希望我跟思思可以早一点分手。”
我的笑容像是风中寂灭的花朵,在黑暗的角落,心里有些什么东西一寸一寸坍塌了。
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其实你身边有别人,所以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牵我的手,人前人后你两副模样,只是不想被人察觉我们之间那点与众不同。
那是我时隔多年第一次再喝酒,喝了很多,最后一个人在洗手间门外的盥洗台上吐得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我想我大概是哭了。
圈子里传言苏瑾是一个从来不会哭的人,其实只是没有伤心的事情而已。
因为曾经失去过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于是养成了今时今日这副隐忍坚韧的模样,可是在这个夜晚,我依然被那种暌违已久的淡淡的羞辱击败了。
这种羞耻,是你给我的。
你沉默地站在我身后5米之外,用手中的相机拍下我此时仓皇的背影,后来你把这张照片洗出来夹在钱包里,当林思思问起的时候,你说是一个女明星。
这些我当时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你递来的纸巾被我甩在地上。
那天晚上小卉她们都很惊讶我酒兴那么好,跟每一个人玩游戏,输了我二话不说就喝,后来大家发现不对劲了,因为我赢了也喝。
你在一边终于看不下去了,顺手捞起我的腰跟大家说:“你们先玩,我先送她回家。”
在你的车上我闻到了Dior甜心的香味,我嘟嘟囔囔地说:“这么小女生的香味……”你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一路上一直沉默。
其实我于心不忍,明明是你的生日,却弄得你这么不开心。
可是要我装糊涂,要我在众人视野之外的地方陪你玩暧昧,对不起,那不是苏瑾做的事。
我下车之前,你忽然铿锵有力地说:“苏瑾,我喜欢你!”
我啼笑皆非,这么容易说出口的“喜欢”,你以为我会有多珍惜?我拍拍你的脸:“亲爱的,我不会当真。”
我只是没有想到,次日清晨,我拉开窗帘,阳光洒进房间,同时,看到你的车。
你在电话里说:“我等了一夜,其实你只要起来看一眼就会知道我一直在这里,但是你竟然真的……”
我干脆利落地摁掉电话,什么都不想说。
其实这一夜,我并没有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直至半夜,又起来把冰箱里剩下的那瓶清酒喝掉了,本意是想喝完之后可以倒头就睡,没想到越喝越清醒。
镜子里那张脸还很年轻,可是我的灵魂,已经老了。
从我干脆利落地挂掉你的那个电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你都没有再联系我。
我不是笨人,飞蛾扑火这样的事年轻的时候可以做,但是长大了再做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所以尽管某些空虚孤独的时候,我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你的笑容,可是理智告诉我,不要纵容自己这样下去。
无数知性犀利的前辈在无数的规劝信条中告诉成长中的女生:别人的男人不要去碰。
我从十七岁开始就懂得的道理,没理由再去越界。
可是在某天跟一群人嘻嘻哈哈的空隙当中,我再次不能抑制地想起你的时候,我知道,我完蛋了。
寂寞的时候想念一个人,不算什么。
热闹的时候想念一个人,这才可怕。
我终于忍不住拿起手机打给你,装作漫不经心问起:“你在哪里?”
你顿了顿,然后说了以前朋友们常去的一个咖啡厅的名字,你说:“过来吧,我想见见你。”
短短的车程,无数次我想叫司机停车,我想半路落跑,这是一场欲望跟理智的战争,最后我发现前者还是占据了上风。
你在街边等我,白衣胜雪,我远远看着你,眼眶里有了湿意。
有句话很土,但是用来说我们却是恰如其分:相识已晚。
在直面彼此的几分钟内我们都没有说话,这沉默却更叫我难过,最后打破僵局的是你,你打开钱包给我看一张黑白照片,我辨认了半天才发觉那是自己。
你说:“是不是很有艺术感?”
我忍不住笑起来,你又说:“特意去了色,总觉得色彩太艳丽了不是你。”
可能是你出来的时间太长了,你的朋友终于忍不住出来一看究竟,你对着我身后招手,我顺势回过头去看了一眼。
这一眼,看得我五雷轰顶。
我没有想过,这一生会再见到周昊予。
我后来的朋友,都知道我不穿高跟鞋,但是她们都不知道,十七岁之前,我嗜高跟鞋如命。
在十七岁之前,我一直坚定地信奉“每个女生都要有一双高跟鞋”以及“不穿高跟鞋的女生人生都不完整”这样的说法。
那个时候的我,完全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我,如果非要选一款香水,毋庸置疑也是Dior甜心,那个时候的我多好,他们都说我纯净得像一块冰一样。
那个时候……我喜欢的那个人,他叫周昊予。
他是城中有名的贵少爷,整个家族都做房地产,人生对于他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相识是因为在某个节假日,我那双劣质的高跟鞋被卡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的下水道缝隙里,我用力一拔,鞋跟断了。
每个女生在年轻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个关于王子的梦想吧,在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拯救她于水火之中。
周昊予对于我来说,便是命运赋予了这样的意义。
我因为窘迫和难堪而埋着头慌张得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从路边的跑车上跑下来,一把将我抱起妥善地安置在他的车内,我因为巨大的震惊而忘记了言语。
多年后我依然记得他提着那双银色高跟鞋朝我走来的时候,脸上那层神圣的光芒。
对此一切,他给我的解释是:你太漂亮了,不去救你简直是白痴。
从此人生翻开崭新的一页,清晰地明了了失去的痛,清晰地明了了留不住的悲。
时隔经年,我们两个人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那样清晰地看到时光在对方身上留下的痕迹,强烈的心酸击倒了我。
过了半天,他终于叫出了我的名字,我笑着点头:“是我。”
原谅我,那一刻,我没有多余的力气,顾及一旁神色从惊讶转为黯然的你。
世界太小了,我怎么都没想到,曾经你无数次提起在国外留学的至交好友,竟然是我青葱青春里深深爱过的男孩子。
你像一座桥梁,顺利地促成了我和昊予的重逢之后,你就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一个落着大雨的午后,昊予坐在客厅里看杂志,我面无表情地在做一道甜品:椰汁芒果爽。我们像两个劫后重生的战友,对于过去那场战争绝口不提。他忽然说:“王宇哲喜欢你。”
我切芒果的手不自觉地停了下来,他又接着说:“苏瑾,无论如何,我希望你快乐。”
冰块在溶化,我依然不知道要怎么接他的话,只能静默以对。
他放下杂志走到我面前,摁住我的肩膀,正色道:“苏瑾,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王宇哲是真的喜欢你,我看到他望着钱包里那张黑白照片发呆的样子……我的兄弟,我最明白。”
“那么……”我抬起头来看着他,“那么你告诉我,林思思怎么办?”
他的脸色一变:“苏瑾……宇哲对林思思有一份责任在,他们在一起很久,林思思家境不好,她家希望她能借助宇哲改变人生。”
我听到这句话忽然开始发飙:“家境不好怎么了?穷人家的女孩子就理所当然要成为你们这些贵公子的玩物?在你们身上耗费了大好年华之后,得到一点物质或者金钱之后识趣地离开?”
我终于说到正题上,昊予的眼神在那一瞬间无比悲伤,前尘往事穿过时光逆袭而来,我们倔犟地对峙着,紧接着,我的眼泪大颗大颗砸下来。
十七岁那年的伤口在回忆面前被剧烈地撕扯开来,我不是不明白,那些伤口一直都在,再长的时光都无法将它们完整覆盖。
是昊予让我懂得了爱情中的美好,同时也是他让我懂得了现实世界的残酷。
在这个下着大雨的下午,他不能自制地紧紧抱住我,我知道这个拥抱的意义,不再像从前那样出于爱,而是出于一种愧疚。
他的声音嘶哑低沉,缓缓向我说起:“后来我终于知道真相,可是我找不到你了,我没有办法亲口对你说一句对不起。”
“到了加拿大,许颜整个人都变了,我一开始以为她是不习惯陌生的环境,可是过了大半年,她还是郁郁寡欢的样子,我甚至都想带她去看心理医生。”
“后来她终于憋不住了,再不说出来她就会疯掉了……苏瑾,其实许颜当初,真的只是不懂事,她本性并不坏,后来这些年里,她一直心怀愧疚。”
“我妈妈知道我这次回来偶遇你,也让我向你说一声对不起,当初她,确实太跋扈了,你知道,居高临下的人,总是不太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
昊予的口才比起当年来好了很多,可是没有用,再完美的措辞,再体贴的理由,都无法磨灭我素白青春上那一抹浓墨重彩的伤疤。
我轻轻地推开他:“不要再跟我说对不起,以前的苏瑾,早就死了。”
许颜跟昊予的妈妈在酒店门口截住我们的那天,正是昊予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前一晚很多朋友一起玩,喝了很多酒,玩得太晚了,我那个醉醺醺的样子又回不了家,只好任由他安置。
我永远记得许颜那时傲慢的眼神和昊予母亲轻蔑的神情,尽管我穿着高跟鞋,可是无端好像矮了几分。
昊予的妈妈并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为难我,而是随手从钱包里拿了100块钱让我自己打的回家,我没有接受那张钞票,但是我的自尊已经受伤。
我一路走回去,新鞋子很不合脚,每走一步都很辛苦,我一路走,一路哭,虽然还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已经意识到要失去什么了。
我相信昊予那时对我是认真的,在他被禁足的那两个月里,许颜找过我好几次,我都躲过去了,最后一次,是在昊予去加拿大之前的一个礼拜,她把在学校上课的我从教室里叫了出来,跟她一起来的还有政教处的主任,那个主任卑躬屈膝地跟在她身后像一个奴才。
彼时,我已经完全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
昊予跟许颜家里几代世交,那种稳固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之上的,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关系远远比昊予在大街上对一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一见钟情要牢靠得多。
满了十八岁,两个人就要一起出国,这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计划好的事情。
生长在大家族,从小就深深懂得要如何规划人生的许颜,断然不会允许一个穿着劣质高跟鞋,喝酒像喝水一样,不知自爱的穷家女妨碍她。
在楼梯口,我们两个人剧烈地争吵起来,她言辞尖酸刻薄,我也不甘示弱,最后愤怒至极的她狠狠地推了我一下。
后来无数个从噩梦里哭醒的夜晚,我都不寒而栗地想,如果我不是穿着一双高跟鞋,在许颜推我的下一秒,我是不是能踉跄几步之后迅速站稳?
我只有这一遭人生,不能倒带,没有如果,不可假设的人生。
我从高高的台阶上滚下去,我的耳朵里只有巨大的轰鸣,眼睛什么都看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很疼,非常非常疼。
躺在医院的那两天,惊慌失措的许颜已经提前出国,而昊予在他母亲卧室门口跪了一夜之后终于以妥协换得了来见我一面。
他怎么都没想到,躺在病床之上,脸色苍白的我,会对他说:“不关你的事,我本身就是个乱七八糟的女孩子,当天肯跟你走,后来就能跟其他人走。”
昊予是愤怒地离开的,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当时睡在病床上,他一定会抽我两耳光。
他走之后我微笑着对在一边哭成泪人的妈妈说:“没事的,爸爸的工作保住了,还额外赚了一笔。”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浓烈的屈辱,昊予的母亲走进我简陋的家,把一张我以前只是在电视剧里看到过的支票摆在我们面前,她的声音不大却极有威慑力,意思非常明白,要么接受这张支票离开她儿子,要么,以周家的权势,随便捏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能让我爸爸的工作单位开除他。
那是我们全家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我明白,这其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从那一天开始,我的人生丢失了两样东西,一是高跟鞋,二是眼泪。
并且,我不再喝酒。
这些刻骨铭心的伤痛与屈辱,是我多年来踽踽而行的原因,我不再向往爱情,身边有女生谈起自己的“豪门梦”,我的心里都会掠过一声叹息。
你在我身上看到的那些自律,那些隐忍,不过是这场青春浩劫留给我的教训。
我自己是那样痛过,便不想因着我,让你身边的那个人痛。
对你,是因为懂得,所以去爱。
对她,是因为懂得,所以不去伤害。
我再次穿上高跟鞋,站在昊予身边,微笑而立。你的眸子里一闪而过的绞痛没有掩饰得好,你脸色很难看,把我拖到无人的角落里,哀伤地问:“是真的?”
我知道你指什么,昊予是不是那个能让我再次穿上高跟鞋的人。
虽然很残忍,但是我点点头:“是真的。”
中国有句古话,当断不断,反被其乱,我再不做个了结,大家都难过。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赌局,适时立场,方可保全自己。
只是,王宇哲,我爱你,从那个游戏开始,我大概就爱上你。
你在厨房里帮我擦眼泪,你招呼朋友们吃坏掉的菜,你在我家楼下等我一夜,你把我的照片夹在钱包里随身携带。
能被你这样爱着,不管是什么样的结局,都叫我安慰。
原谅我的懦弱,我不能做飞蛾扑火的爱情圣斗士,通过伤害无辜的人来成全我的快乐,这样的事情,我做不来。
然而,这些,你未必明白。
最后离开的时候,你的语气里满是苦涩:“你开心就好。”
你真的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有腔调的对白,可是我给你的那些笑容都是发自肺腑的,你离开之后我脱下那双让我发抖的高跟鞋,蹲在墙角哭得像个白痴。
昊予站在一边看着我,什么都不说。
我以为这是我们之间最好的结局,优雅的,从容的,妥帖的。
直到我收到那封快递。
事后昊予跟我说,你有这个习惯,每次出行之前都会写一封信给心里最挂念的人,因为你从小就怕死,更怕死了之后有些话来不及说,如果没有意外发生,三天之内你会通知快递公司收回那封快递,这些年来,从来都没有人收到过你的信。
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那封信很短,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字,苍劲有力,整洁干净。
你说:苏瑾,我们之间,算是有缘无分吗?是时间弄错了吧,你爱着别人的时候,我懵懂无知,我身边有别人的时候,你心如死灰。
我这一生吊儿郎当,没做过什么善事,除了深爱你,不求回报,如果这也可以算是善事的话。
苏瑾,我真是希望你过得快乐。
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可是每一个字都像子弹穿过我的心,我握着那张薄薄的纸,几近昏厥。
那张黑白照片从信封里跌落出来,背面朝上,我看到那句诗。
IfIshouldseeyou,afterlongyear.
HowshouldIgreet,withtears,withsilence.
(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是1.521亿千米。
月球到地球的距离是384,400千米。
而你我之间的距离,是一张黑白照片。)
无论如何,我不相信你就这样告别,这太戏剧化,这个结局不符合我这么务实的人。
我日日夜夜沉溺在酒精之中,越来越寂寞,越来越清醒,小卉她们找过我很多次,最后大家都放弃了。
王宇哲,谁都不知道,我喝了酒之后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你的样子来,你嶙峋的轮廓,清亮的眼神,你的一点一滴,清清楚楚,毫发毕现。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回来,就像那首诗写的那样。
只是我该如何贺你?
以沉默?以眼泪?
还是淡淡一句,别来无恙……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六月,安好!
- 简介:主人公黎梦汝身世曲折,可知道遇见了那个他给他泼冷水,校园的一切的一切让她悲惨的人生更是雪上加霜……
- 0.1万字2年前
- 大学杂文
- 简介:记录一些作者大学的所见所闻所感
- 0.2万字2年前
- 普樱圣学沐学院
- 简介:一切如浮云他和她的爱恨情仇,六人的友意比什么都好,一见面比天大。分了还有什么重要又和好。没见面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谁,一见面的时候,从友情到爱情分分合合,她和她的故事又会怎么样的发展呢?
- 0.9万字2年前
- 星界事务所
- 简介:嘶……希望我会成为,最棒事务员!
- 0.1万字2年前
- 大千世界之成神
- 简介:身份神秘的少年穿越到了大千世界中,面对挚爱他又会怎么样抉择?是重走老路还是,为她屠尽一切神魔?
- 0.2万字1年前
- 斯荏若彩虹,遇上方之侑
- 简介:传说女娲用石补天时,彩色的粉末散落天空变成彩虹,拥有着特殊的魔力,在彩虹下相遇的两个人会堕入爱河。
- 0.3万字9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