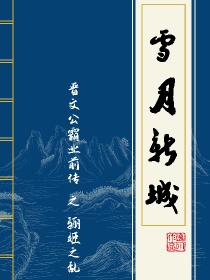第九十章 告别
我这辈子仿佛与女人相克,我的母亲,我的祖母,我的妻子,甚至于我的妃嫔姐妹和女儿,一旦碰上女人不是我不好过便是她们不好过,不晓得是沾了什么倒霉的运气。
即将离宫出巡的档口,我还是忍不住见了一回皇后。
皇后已被幽禁了一年有余,再见她时已不复昔日年轻美丽,此时一身素淡的青裙,翘着腿倚在烈日的树下,以脚尖逗弄着一只唤“阿宏”的幼犬。
“阿宏,你尝尝这杏子,这杏很好吃哪,你幼时最爱姊姊姊姊地追着我要呢……来,尝一口好么?”
阿润咬下一口杏吐在手心,那小犬听到招呼摇头摆尾地凑上来,却是嗅了嗅,又默默跑开了去。
“你这个小东西!”
阿润气得直跺脚,吓得那幼犬噔噔噔地跑到了我这处,待与我这个不速之客对上眼,又“汪汪汪”地吠了起来。
“阿宏?”
我抱起脚下虚张声势的小犬,黑洞洞一片中一美妇人走了过来:“阿宏……好久不见。”
当真是好久不见了。
晕眩消去,我抚着怀里安分下来的脑袋寻处坐下,诡异的沉默里看向对方手中。
是被咬了一口的杏。
我少时的确爱吃杏,只要是杏,再酸涩的也都爱吃。
阿润见我看那杏,顿作欢喜地递上前:“我晓得你爱吃,就摘了些,房子里还有,你要的我我再给你取。”
她与我没心没肺地笑道,仿佛从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的皇后对我毫无威胁。
我早知道,早在八岁那年她递给我杏子的时候就知道了。
她不类她的姑母,她的姑母嫌她纯挚傻气,十四岁那年进宫不过一月便借口将她撵了回去,后来太后过世,我迫不及待地借口让她进了宫,再后来废了她的姊妹,扶持她做我的皇后。
魏国的皇后只能姓冯,是我与病榻上太后立的誓。
阿润并非心机深沉之人,所为的一切都在旁人的计算之中,于是分明身为高门贵女,姿颜无双,最后却只落得空有皇后之名而幽禁此院,如今与我成为怨偶,算是因此蹉跎了大半生的年华。
若是十分地痴傻便也罢了,于她我全作长辈奉养也罢,偏偏只有五分……
我未接那被咬了一口的杏,招呼着她自我身旁坐下。
“今日还是想问,你到底爱不爱我呢?”
阿润却不若第一次那般激动,这次眼皮落寞垂下,只不冷不热地答了句“不爱”。
“爱又如何,不爱又如何,你又不会放了我。”
阿润柔丽的眼角翘了翘,手下耐心地抚着膝头小黑犬的脑袋。
她并不与我有什么好气,一如既往随便就暴露出了自己的心思:“我只盼着你死,你死了我便可以解脱了,届时我带着我的阿宏出宫,谁也管不着我。”
出宫?
出宫再寻一二十个面首么?
亦或是,还当我是她那十来个面首的其中之一?
哪家的皇帝是如此活法,我恐怕是头一遭罢。
我被她气得发笑,如此一通打击心下遂也有了底,拍拍身上的尘土孑然起身:“你也不必等我死,现下我便放你走。从此我当我的皇帝,你当你的民妇,咱们桥归桥路归路,以后谁也莫再惦记着谁的什么了。”
我不贪图她的颜色,她亦莫贪图我的富贵,我们再无瓜葛。
违背誓言又算得了什么,都到如今这个地步,我还有什么可畏惧的,不过一死而已。
“阿宏,阿宏你等等……”
身后女人的呼喊里我头也不回逃出了后宫。
这幽暗龌龊的深宫,我再不会回来了。
我按着扑通扑通的心口上了车,车内的六弟尚支着脑袋打盹,听到动静悠悠醒神,自坐旁的匣内取出一瓶:“大兄脸色不好,服些药罢。”
这药是阿勰怕路途不便,特地吩咐医士做成的蜜丸,以备不时之需,未成想出发的第一日便用上了。
我服了药唉声叹气地躺下,心事落下脑袋也昏沉起来,听着外头一声清脆的扬鞭,心知是准备启程了。
此行急也不急,是打算去往关西巡视同州华州等地。
齐国我最大的对手萧鸾一死,其子萧宝卷不成气候,我此时趁着他们国内生乱之时西巡,一是经营关中之地,为以后的伐蜀做准备,一是要质问两年前趁乱叛降蜀地的杨灵珍,要齐国给我一个说法。
若能取得汉中和巴蜀,荆益之地得手便容易多了。
贾谊此人,无愧国士也。
马车渐渐跑得快了些,我卧在车内昏昏沉沉地思虑我的天下大计,四月的天气消磨到午时都有些热,阿勰不知哪里取来一把蒲扇,不疾不徐地为我扇起了风。
微凉的风拂过我的鬓边,我嗅着空气里淡雅的香懒懒问他:“这香甚是好闻,不知是如何制的?可否赠为兄一些哪?”
风停了下来,阿勰已将蒲扇纳于襟前,肃穆与我禀道:“大兄疾患未去,臣并未熏香。”
哦,没有熏香?
我没耐住心下的奇怪坐起身,捉住他的袖嗅了嗅,无香,又自脑袋到浑身嗅过,却也无香。
那怪了,我方才闻到的莲花香是哪里来的?
阿勰被我的无理取闹羞红了耳尖,玉色的脖颈亦赤了起来。
暮春的空气有些暖热,我不知诡异之处,照旧欲与他调笑:“此当是贤士之德馨……”
我话未罢额前软凉一触。
阿勰吃了蜜糖似的舔了舔唇,酒窝情不自禁地显现出来:“大兄亦馨。”
(双男主)白莲花养成记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囚府梨园
- 简介:男主顾灵译与女主夏意因五年前的纠纷,男主强娶豪夺,强制爱
- 0.1万字1年前
- 乱世玄音
- 简介:一名游戏爱好者,在偶然的一次机会中,一道紫电从空中划过,他穿越了,来到了三国乱世,那么,就看他如何平定乱世吧
- 1.6万字1年前
- 雪月新城:桓庄之族的覆灭
- 简介: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五千年风华烟雨,是非成败转头空!春秋初年,曲沃代翼尘埃刚刚落定,晋献公初登君位执掌权柄,处处受到公族的掣肘制衡,君臣之间互相角力,一场残酷的宗族内斗呼之欲出……本书是《雪月新城》系列的第一部:桓庄之族的覆灭。
- 4.9万字1年前
- 三国之我不是后主
- 简介:刘备:若阿斗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陛下你胡说什么呢!太子堪比秦皇汉武呀!曹丕:刘备有子如此,玄德未死也!孙权:生子当如刘公嗣,我的儿子都是猪狗一样的人物啊!司马懿:肃清四海,总齐八荒。司马氏才是天命之所加也!刘禅不屑地笑了笑:子上,颇思晋否?司马昭猛吸一口五石散:啊……此间乐,不思晋!
- 2.4万字1年前
- 我的手机通千古
- 简介:二十一世纪宅男/女意外得到了一部手机,没想到居然联通过去与未来!预知中奖彩票号码?知道股市?成为百万富翁?实数低配!干扰雷达、截取情报才是算是重头戏!再加上预知未来大事件、世界趋势,登上历史舞台不在话下!来看看咸鱼宅男/女是如何凭借一部手机,咸鱼翻身,走上人生巅峰的吧!
- 0.1万字1年前
- 中国驻印军
- 简介:1941年12月23日,为了保证中国对外交通线的畅通,中国和英国达成共识,在缅甸反抗日军的侵略,由于英国军队胆怯日军,和中国远征军其他军队迟迟没有到达指定位置,导致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损失惨重,错失了同古会战,密支那会战,曼德勒会战等消灭日军主力的良机,从而被日军赶出了缅甸。1942年,在中美英三国的联合下,中国驻印军组建起来,粉碎了日军在东南亚的侵略
- 4.9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