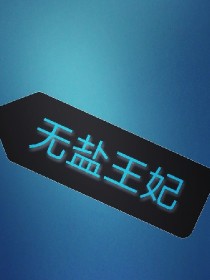116谁对谁不舍一
116.谁对谁不舍(一)
这日浓雾锁地,黎明之时,日夜交替之际,一阵马铃由远及近,破开晨雾。都城的人们尚在酣梦中,不知外面正有一队威武车队行过,车马披金挂红,充满吉庆,却无论是人、车、马,清一水儿的戎狄家什。
街石干干净净,马蹄踏上响声清脆,马儿好似不愿惊破宁静,连响鼻也不曾打得一个。街边有格外赶早的买卖,已经张开了铺子,西尤跨马行在车边,问:“难为你醒得来,那里有买卖人,可要吃些什么?”
车内无人应答,仿佛一辆空车。西尤却微微一笑,鞭儿快活一甩,小跑至队伍前头。
朝阳升起,扈烈正副使者及哈刚木等一众要员进宫面圣未归,索欢在第二道宫门外等候。他在车内,精致的妆面遮不住苍白脸色,身旁草原女子打扮的侍女正为他擦汗喂药。
这侍女不是旁人,乃是宛淳,她将头上的高高长长的顾姑帽一把掀在车内软榻上,生气道:“什么怪帽子这么高,戴也戴不稳,还老顶着车蓬!”硬是叫满面忧戚的索欢笑了出来。
“车马劳顿,公子笑一笑也好得快些,否则可难支撑这一路。”
“支撑不住更好,叫他们折腾去。”索欢苍白一笑,摇摇头不让喂了。
宛淳不知他使命在身,以为他存心糟蹋身子和扈烈过不去,打起车帘来望一眼车外守着的扈烈武士,她悄悄劝慰:“公子再舍不得大人,如今也这样了,不如看开些,跟着西尤将军也是一样的。若说人才,自然是宰相大人好,但要论有心,只怕是西尤将军更胜一筹,远的不说,就说昨儿,公子要走了,大人还不愿饶恕,硬把公子欺负成这样才解恨,哪管你的死活?反观西尤将军,虽是北人,倒不是一味粗鲁不疼人的,昨日见公子伤了,赶紧着人请医、号脉、抓药、煎药。今早动身,时间那样紧迫他还赶着吩咐我,叫我一路上费心,若有半点不好,他只和我讨命——您听听,要和我讨命呢!公子就算不为自己打算,也要为我想想呀!”
我昨晚就剩半口气,他若还粗鲁不讲理,只怕要拖着具死尸上路了,索欢想着,拉住宛淳的手抚摩,“淳儿不同一般女流,连夷狄虎狼之穴都敢和我去,多谢,我一定保重自己、保全你。”
“公子说话就说话,摸我的手干什么呀?”宛淳藏起手不高兴道:“公子谬赞,其实我心里害怕得很,且不说这一路如何,只说背国离家四个字。可眼见公子浑身是伤,不得休养就要动身,公子是无忧姐姐的主人,如今也就是宛淳的主人,岂有奴才看着主人吃苦的道理?再来我服侍公子惯了,公子一去,我心里空落落的,我想公子也一样,路途遥远,身边一群爷们儿,又糙,又彼此不了解,又语言不通,哪里使得着?少不得要受罪的,所以我才求宰相大人打发我一起来。”
索欢让宛淳坐他身边,宛淳摇摇脑袋。这马车只容一窄榻,索欢歪着就占了大半个,她不肯与他同榻并坐,老躬身站着,高高的帽子才时不时碰着车顶蓬。索欢道:“你不必与我拘礼,我知你心里有了无忧,不肯同男子亲近,可对着我你怕什么,便解了衣服睡一觉也只是互相暖被窝罢了。无忧从不与我讲究这些,有一年腊月,我病得沉重,又没钱买药,全靠她夜里抱着取暖才捱过来的,要照你这么想,我病死了活该,她该死守礼数。今儿你倒提醒我了,男女大礼不可越,何况肌肤之亲,我或该娶了她才是。”
宛淳听见最后一句话,忙身子一矮一屁股坐下。
“这就对了,”索欢轻轻靠在她的肩上,“难道忠贞只在皮肉碰与不碰么?说得粗俗些,心给出去了,躯壳算得了什么,纵然千夫……”他突然住了口,心想淳儿毕竟是正经闺女,虽然知道那种事,但妓子的那套糙话,还是少听为妙,人家纯情专一,没的学坏了,倒是天大的罪过。连忙笑着改口:“淳儿自然是懂礼的好女孩儿,别听我的混账话。守礼是对的,却要分人不是?我半个女人一般,哪里需要你守什么男女大礼?像拐着弯子骂我不算男人似的。”
“公子又多心了!”宛淳纠结了片刻,叹道:“也罢,以后我还同以前一样待你。”她亲昵地用手背擦掉他嘴角的药汁,道:“公子方才道谢,宛淳实在有愧,我跟着公子固然有担心的缘故,却也不乏为自己谋出路的意思——公子是明白人,宰相大人现在对你如何也不必我多言,只是我服侍公子这么久,宰相大人还能见得我?我害怕,与变成大人的眼中钉,不如自己识相些,跟公子远远到异邦去,让他老人家眼不见为净罢!”
“凤大人厌弃我,你怕受连累,这是你有算计,无可厚非。”他语气坦然,说完却一口气哽在胸间,没命大咳,直咳得泪花溢出,力倦神微靠在榻沿上倒气,宛淳忙拿药碗叫润嗓子,索欢挡开,气息微微道:“哪有用药润嗓子的,你扶我躺好歇歇儿是正理。”
所谓躺好,他全身有伤,自然不能舒服地平躺,宛淳将他侧卧着,拿层薄毯盖上。移时,索欢睡了,她跳下马车撒目一看,顿时被这巍峨庞大、森严静肃的宫城激得心潮澎湃。
天晔禁宫名太康,尚黑尚金,宫墙被浇铸了一层铁水,上铸各式龙图腾,施以黄铜,或填以寿石,或嵌以云英,各色龙图腾在黑底的衬托下瑰丽醒目,威势慑人。今日广场上四面飘扬着长长红绸,训练有素的宫人们在中轴正道上快速铺好红毡,沿途立满盆花,皆为牡丹名品,宛淳看得啧啧摇头,这真是嫁公主的排场!
这时,一队侍卫挥舞马鞭小跑出城,宫人肩抗扫帚等洒扫用物紧随其后,宛淳侧耳,隐隐听见城外此起彼伏的买卖吆喝声——宫外的街市摆起来了!她同许多相府家奴一样,打脱胞衣没出去过,精致高贵的东西见过不少,最平凡的反倒稀罕,即将去国离家,突然很想去闹市逛逛,看一看凡俗烟火,故风人情。
王宫外本不许摆摊开铺,然而长久无人严管,百姓便一里儿一里儿地围了上来,好在太康王宫有内外两层宫墙,内外墙之间夹一片停放王公贵族的车轿马匹的阔大草场,宫外尘嚣根本传不到内宫里,再则外宫墙的禁卫爱热闹、图省事,平常日子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今天这样的日子是不能含糊的,侍卫们一队队奔上主街鸣锣警示,然后就是一阵喧天的鸡飞狗跳,大概是在驱散百姓。
宛淳忙往宫门跑,她要看一眼集市的样子!才跑几步就被看守的扈烈武士喝住,她遥遥凝望宫门,看着高入云天的城垛,看着城垛上猎猎卷动的仪旗,一瞬间,少不知愁的她热泪如涌。
车内,索欢亦眼泛热泪,可他此刻的心思与宛淳相比就显得小气了——将一条手帕缠在指间,又贴在脸边,贴到脸边怕弄脏了,赶忙揣回胸口,揣回胸口却舍不得,忍不住又扯出来,真是反反复复做足了小儿女情态。要在以前,他非啐自己不可,现在却浑然不觉矫作,只把物品看成人,当做与那人同行。
这是凤栖梧用得最多的一条手巾。自他们好上后,他发现他很爱干净,袖里永远有一块简单的织物,会不时地拿出来擦一擦手指,同时,他毫不介意给索欢清理,飞灰、泥土、汗迹、泪水,十分动情的时候,甚至直接用手清理他们事后的液体,每当索欢看到他用那双保养得毫无瑕疵的手一点点揩去自己身上的秽液时,就觉得这个男人非常帅,非常地特别。
真是一个温柔的大坏蛋。
索欢咬住被角,按着胸口重重一撕,疼得浑身痉挛,内心却充满了献身的甜蜜:这是你给我的印记,不想让它好……
思绪飘飘摇摇回到昨日,他几番示好均被无视,连凤麟夹在中间都如芒在背,他怎能再热脸贴冷屁股?故而部署一结束就赶着告辞,方到门口,凤栖梧却淡淡一句:“你很喜欢耍人?”
——你很喜欢耍人?
耍人么?索欢折回去望着他,看到那冷漠的眼眸下迅速闪过一丝痛苦和责怪。几乎本能地,他岔开腿往后一倒,躺在羊皮地图上笑得满脸坏水儿,“耍人是谁?我喜欢的是凤宰相。”
凤栖梧冷笑一声。
“真的,我不喜欢耍人,我喜欢宰相。”
凤栖梧不为所动。
“喜欢他,却让他难过了,怎么才能重得欢心呢?”
凤栖梧轻蔑地睨着眼。
“大人给些建议吧,怎么做才能让他原谅我。”
真是见鬼!凤栖梧恼怒地扔出一支匕首,不偏不倚斜插在索欢张开两腿之间。“喜欢的话先闭紧大腿吧,本座可不想你这丑模样落在西尤都敏眼里。”说罢用力甩一下衣袖,带着凤麟匆匆离开,留下一脸愕然的索欢。
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索欢有点控制不住双手的颤动,用力起出胯下匕首,看看凤栖梧离去的方向,又看看手中闪着冰冷光芒的刀刃。
黄昏了,思来居管事正派人洒扫庭院,忽然一个人影撞到身前,抬头一看,却是索欢——他的脸色苍白得如同一张白纸,额上涔涔冒汗,身体摇摇欲坠,随时要倒下的模样,然而眼瞳精亮,洋溢着不同寻常的光彩。
“管事老伯……大、大人呢?”
管事摇摇头,想告诉他大人不在这里,却突然看见他的淡粉衣裳下面冒出点点红色,如同画梅时宣上的红色墨点晕开。管事揉了揉眼,他见过索欢这件衣裳,男儿款式,女子配色,两枝海棠压在肩头,飘落花瓣片片,极富层次的淡红色搭配,纯银线的编织腰带,阔袖收腰,衬得清瘦瓷白的他鲜妍修挺,有一种矛盾的仙风妖骨。
绣的海棠怎么能开出红色花朵?管事定睛一看,吓得瞪大眼:“你在流血?”索欢晃了一晃,他连忙托住,扬声道:“快来人,送公子回碧萝苑!”
索欢抓紧管事手臂,“不,大人呢?我要见他!”他一使力,手臂的位置又冒出几道血点。
“大人没来书房。”管事看看四周,好几位打扫的男仆均已停下手中活计,纷纷看着这里,他压低声音道:“回去吧,扈烈使者的事我们大体知了,大人不会因为你受伤就收回成命的。”
索欢闭眼微微摇头,“烦请管事老伯告知,大人在哪里。”顿了顿,哀声道:“你是管事,肯定知道的对吗?”
管事犹豫片刻,吩咐左右道:“去定璘湖找找看,有人看见大人往那边去了。你们去请示大人,问他可愿见索欢公子。”
“有劳了。”索欢拱手道:“大恩不言谢,救火那晚多亏思来居的众位冒死拦住大人,诸位情深义重,索欢有生之年必当报答!”说着飞快地跑走,完全不像一个受伤之人。
“阿风!你怎么了?”
管事转头看去,是那位寡言少语却颇有才学的年轻人,正杵着竹扫帚从地上站起来,并对搀扶他的同伴摆手强笑道:“没事,一时晕眩,坐一会就好了。”
他近来黄瘦不少,精神也差,像棵蔫菜一样,却仍然手脚勤快,对人谦逊,管事很喜欢这样的年轻人,忙着人带他回屋歇息。
“不成,我们还要去定璘湖寻大人。”左右故意道。管事抚须一笑:“他都去了你们还去作甚?接着干活儿吧。”
傍晚的风穿过树梢,拂过藤萝,掠过定璘湖的片片鳞波,带来湿润的凉意。凤栖梧侧靠坐在定璘湖心的小亭里,对着一群泛游的沙鸥自斟自酌,须臾,他将一管竹笛横在嘴边,清丽曲调徐徐响起。索欢不想破坏这场面,偷偷躲在藤萝后观望,他听过这调子,仿佛是《鹧鸪天》,喜来擅长管乐,把其中的滑音玩得相当漂亮,还能即兴发挥花舌音,配合鼓点与筝鸣,明澈笛曲变得非常富丽。凤栖梧的笛音却不一样,刻意放慢的拍子平实悠长,幽游低徊如同在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索欢沉浸其中,忽然闻得一声尖锐破音,调子骤然拔高,湖面沙鸥被惊动,“呼啦啦”纷繁而起,翅膀切割夕照,扇动的气流扬起吹笛人的轻衣墨发,一瞬间光影流连,俊美得不可方物。
索欢趴在叶子缝隙间,痴呆得像个傻子一样。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惭愧——跟他比起来,自己简直就是泥坑里的蛤蟆!他垂下头,不敢贸然上去,不敢毁坏他带来的孤高绚丽的质感。
凤栖梧却要破坏这一刻的美好,手指跳动轮压指孔,迅速变换音调,笛子顿时发出坏了似的短促音节,宛如一个中气不足还夹着破嗓子唱歌的人——他仿佛觉得有趣,吹的时候怎么也隐不住唇边笑意,笑意越来越明显,以至于终于吹奏不下去,放下竹笛饮一杯酒。
可怕的笛音戛然而止,余音却久久不歇,索欢捂住嘴,表情难过得快哭出来,他抓住最粗的藤条,却还是支撑不住,顺着藤条虚软滑下,蜷进密密的叶中。
这首小曲,是他们最好的时候,他唱给他听过的……
南风阁之公子欢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乾雪恋——d085
- 1.0万字2年前
- 明月不相逢
- 简介:皇朝女帝唯一的女儿任蘋娍貌美无双,胆识过人,原本是下任女帝唯一的人选。奈何女帝被奸人所害,一朝皇朝改姓,任蘋娍被迫成长,家仇国恨,她一路奔走最终遇见谁,又会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呢?
- 28.2万字2年前
- 凤主临,江山定
- 简介:【已完结】山河终将换了新颜,盛世终将如人所愿。这一场乱世兵燹,火雨纷飞,刀光剑影,爱恨情仇,如烟火绚烂一瞬,痛快淋漓……“从今以后,天下间不再有卫国了,你跟着我,总有一天我会送你一个真正的盛世。”“祁北,我会还这世间一个太平安稳。”“我绝不会让北域蛮夷踏入中原一步,死在北疆防线上正是一个好男儿的归宿。”......天下为局,诸国为棋,各人有各人的信仰,各人有各人的坚持。惟愿,故事里的男男女女,心有所向,梦有所往,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架空,架得很空,不要考据嗷。)
- 50.8万字1年前
- 无盐王妃
- 1.4万字1年前
- 太子妃养成计划
- 简介:这就是太子拐太子妃吧?!好甜!!!
- 1.9万字1年前
- 山海经.女丑的恋爱小贴士
- 简介: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山海经.海外西经》《山海经》上写羿射九日,《山海经》也写女丑被十日晒杀,于是就有了这篇脑洞大开的故事。后面会有众多角色出现,至于男主是哪个,还要看各位看官的意见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感恩的心感谢家人。
- 1.8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