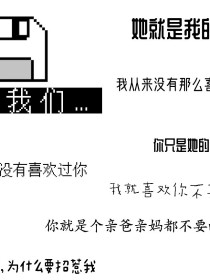Z先生(九)
我明明在说我十七岁的事,却总是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十九二十岁,还总是说着说着就哭个不停。
我可真是矫情啊。
属于十七岁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离家很远。
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十二月的月底,我们离家坐了五个小时的车来到了艺考的考场附近。
那是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就像一只被突然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鸟。
我没有感到恐慌,也不觉得害怕,我只觉得心里有一团火,随着离家的距离越远而越烧越烈。
我跑去烫卷了头发,还染了个浅棕色,并打了耳洞。可能是因为我凝血功能不太好,愈合能力又太强,平时对它又太残暴,那个耳洞长了两年都不太能取下耳钉。
怎么个残暴法呢?就是耳钉掉了没几天,我发现耳洞已经长愈合了一半,于是就重买了耳钉直接重新按穿,然后想取下耳钉的时候又发现它被血凝起来了摘不下来,于是抓住其中一头就直接拽。
也无怪乎我养了两年。
因为它被我手动刺穿了好几次。
我在感情上非常矫情,但在身体方面又非常漠然,所以我总是无法理解那些破了个口就大惊小怪的人,就像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能因为一件件小事委屈成这样一样。
艺考的那天,是12月30号,那天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很大的雪。
我们大概五点半就开始集合,大家背着画具摸黑往早餐店走。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画具里包括了画板画架画笔水桶橡皮擦和二十四色水彩颜料以及白色颜料。
很重,非常重。
动身的时候我蹲下去背好它之后就没站得起来。
本来我想叫人拉我一把,师兄却直接把我的画袋拽过去了,他前面背了一个,后面背了一个,还丝毫不费力似的。
我默默地接受了他的帮助。
我们吃完早餐的时候地上已经铺上了一层雪水,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谨慎,那天我非常失策的穿了一双不太防滑的鞋,走几步就要滑一下,致命的是我还瞎,那种光线下我几乎分不清楼梯和平地。
于是师兄牵住了我。
想想也觉得他好难,背着两个人的画袋,一前一后的夹击着他,还要分心照顾我,以及在雪地里保持住平衡。
我们考试的地点在十一楼,电梯停用,必须一步一步爬上去才行。
十一楼还好,最高楼其实是十三楼。
师兄和我的考场不在一栋楼,进入考场又必须要排队,所以到地方后他不得已只能把画袋还给我让我背着,并啰啰嗦嗦的叮嘱我的室友看着我。
室友当时打趣道:“行了师兄我知道了,你搞得像托孤似的。”
师兄这才不放心的松开了我。
然后我一踏上一楼走廊(那是很光滑的地板砖)就险些滑倒,幸好室友及时拽住了我,我当时下意识回头去看师兄,却发现师兄还在不放心地盯着我,眼中是肉眼可见的担忧。
最后是室友催促师兄快去他的考场排队,师兄见我已经扶稳墙壁之后才离开了。
那时候我在想什么呢?
不可否认,我一定想过师兄这个人真好,要是真的和他在一起了我一定是被宠着的。
但那时候Z先生的声线和性格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何况我在C先生之后就不会再允许自己犯下见异思迁的错了。
出轨是不对的,我要抗住诱惑。
但我又忍不住想,我和Z先生只是网恋而已,只要我不愿意,他们谁也不会知道对方的存在。
嘘,我在听风说起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菇凉如命亦如梦
- 简介:新手写作,有些地方文笔青涩,见谅然后就是,这本书的章节,这本书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的章节名字是一样的主要是我,想不到那么多名字,而且就是说,每一部分的章节名字都是代表着女主所经历的最后,除非有重要事情,会断更,一般是一定会更新哒哒哒
- 5.5万字2年前
- 迷你世界之童心无邪
- 简介:别问我为什么安吉洛斯是主角,可能是因为手滑,反正主角是谁都无所谓。而且,校园言情的话,可能还要等个几季。因为,主角和配角们年龄有点儿小。
- 1.3万字2年前
- 关于我们…
- 简介:“一直以以来,我都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是,我只把你当成她的替身”“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我放过你,你放过我”“我喜欢你”“我只想一直保护你,不管以谁的名义”“你不过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罢了”
- 6.4万字2年前
- 如此可爱的我们(续写弹簧cp)
- 简介:这人很懒,啥都没写。
- 0.2万字2年前
- 木吉他的弦鸣
- 简介:她的一生都活在冬天,偶然的一天,一颗星星闯入了她的频率,成为了她一生中唯一而短暂的夏天
- 0.5万字1年前
- 腹黑叶少:甜蜜宠爱
- 简介:不小心走错了卫生间,还倒霉的让她卷入了一男一女的是非。拿她当挡箭牌?行吧看你帮我把礼服改好的份上这事就算了!但是嫂嫂?什么鬼,她什么时候做别人的嫂子了!
- 4.0万字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