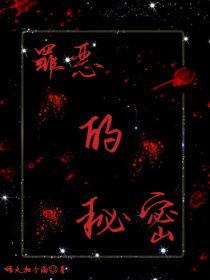第017章又见乌拉草
当我睁开眼睛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那雪白的床单上,身边有两个人,拽着我左手的是生母,拉着我右手的是养母。
还有一个头上有一撮撮白发背微驼的男人,拄着柺在病房外走廊里来回地走,那是我的养父。
后来在O省K市某艺术学院任教的杨柳青老师,还专程来医院里看望了我。
我终于确认了,这个慈祥的老太婆,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外婆。只是有些不好意思,我这个小字辈的没来得及先去看望她老人家……
我觉得必须好好养伤,好好活着,因为我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着。
留在医院里照顾我的基本就是雪儿了。
养父养母毕竟有一份工作,按部就班的,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他们只能在周末来看望我。
好在伤的不算严重,主要是皮肉之伤,每天输几瓶点滴,消炎去肿。医生说:正常情况下,半个月以后可以出院,务必安心静养。
正是梅雨季节,连续几天下雨,窗外豆大的雨点敲打在美人蕉的叶子上,犹如敲打在我的心上。
说是安心静养,躺在病床上的我,却如坐针毡,度日如年。
我在想,出院以后何去何从?还要去米国完成学业吗?可是我和雪儿都面临着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如何维持下去都成了问题。
忽然我的手机震动了,有短信息提示,我的银行账户上有一笔一百万元进账。
接着又有一条短信,是黑豹发过来的:我通过乌拉草了解了你现在的情况,别硬撑着,毕竟我们曾经是朋友,秦少吩咐我暂汇给你一百万元。希望你早日康复重返校园。
自从发生了那狗血的一幕,我以为与秦少彻底撇清关系了,应该连朋友都没得做,不可能再有交集。
我要不要接受他的捐赠呢?我非常纠结,我非常困惑。
真是活见鬼了,我正恍惚之际,失踪多日的乌拉草风尘仆仆地走进病房,还领来一个头发全白,双眼都瞎,手里还揣着一把破二胡的男人。
乌拉草告诉我:“这个人就是阿炳,请转交雪儿验证……”
乌拉草来的真不是时候,雪儿去超市买卫生巾什么的去了,因为我那讨厌的大姨妈来了。
来无影去无踪的乌拉草离去时,还留下一张金卡,说是哈总恐怕用不上这个了,算是哈总对你们的补偿。还告诉我:密码是雪儿的生日。
于是雪儿又多了一个要照顾的病人,那就是阿炳,那个传说中是我生父的人。
至于乌拉草交给我的那张金卡,我随后刷卡(医院里有银行取款机)查询,余额足有10亿元,我以为我看花了眼,反反复复地数1后面的0之后才确认的。
我张大的嘴巴半天也合不拢,太不可思议了。
把这张金卡揣在手里就像烫手的山芋,如何处置这笔巨款成了我的心病。
最终我与生父生母和养父养母商量,大家一致同意全额捐给希望工程,但愿能给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们有所帮助。
当我捐出这笔巨款之后,不到24小时,O省k市刑警大队重案组的人找上门来,还要我们做笔录。至于这笔巨款其实是脏款,并非是哈某的个人合法资产,其中大部分是哈某采取将固定资产多头抵押的形式,从多家银行套取的贷款,好在你们没有占有,就令当别论了。
重案组负责人还向我们通报了案情:哈某在狱中咬舌欲自尽,在送往医院抢救的途中,被同伙策应劫走,负案在逃,很可能易容变身。如果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请速与在此布控的便衣警察联系……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许多人许多事超乎我们的想象,不是我辈凡夫俗子所能掌控的……
我和我的奇葩男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荒野西寻
- 简介:【原创】十年的光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它足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从萍水相逢到兄弟一场,古鑫只念张栋的好。他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古鑫时时刻刻都记在心上。古鑫视张栋为大哥,同时也视为自己的榜样。十年里古鑫的生意做的是大起大落,时至今日走投无路才想起张栋给他的东西和说过的话……从林立都市到浩瀚密林,古鑫进入一片崭新的荒野世界。一路长途向西,跋山涉水一千多公里,只为寻找相隔十年的哥哥张栋。他只为张栋兑现当初说过的话,还是其中另有隐情?毫无生存经验的古鑫,是否能够平安找到张栋?
- 6.2万字11个月前
- all航:罪恶的秘密
- 简介:剧透不是好孩子,自己去看第一章
- 0.4万字1年前
- 去尘决
- 简介:倒计时结束的时候,就是新的开始,且看高尘无敌世间。
- 1.2万字11个月前
- 我的师娘,我来宠
- 简介:陆少三年前因跑路,卷走了师娘公司的全部资产,他不知道,自己带着钱走后,师娘这些年,过的苦,陆少起乘,抱起师娘,师娘,我不会告诉你,这些年我卷走你的所有,就是为了得到你的人。
- 0.2万字10个月前
- 他的样子……
- 简介:女主有个暗恋了三年的男生阴差阳错下她成了芜大的校花男生是校草。在多人的撮合下,他们没有在一起。男主似乎在等她的回应但她无情的拒绝了……
- 0.1万字10个月前
- 奇妙道士游都市
- 简介:顾崇,一位神秘的道士,在受师傅之命下山与师兄们会面。而他去往之地,是华夏数一数二的大都市,清海市。
- 0.2万字9个月前